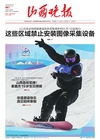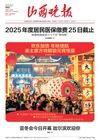香菜和基因
我是个外貌老成、思想老派的老灵魂,唯独在饮食上带着孩子气,恣意、挑食,但偏不怕青椒、茄子和苦瓜;别人的天敌通常是我的“天菜”,芹菜也好,香菜也罢,或许我喜欢的不是气味与口感,而是它们和我一样,没那么讨喜。
据说讨厌香菜和基因有关,香菜里含大量的醛类物质,基因为“OR6A2”的人,吃起来就是泥土和虫子的味道;反之则觉清新爽口。因此香菜没有中间选民,只有爱憎分明的受众,爱者恒爱之。不过反对者的感受也没错,尽管香菜是最早被运用的香草植物,但其英文名“cilantro”便源于希腊字“karis”,意思是“臭虫”。
遗传乃天生,却非不能转化,有些人长大后忽然能接受香菜了,或许大人就是善于忍耐。能吞下原本如鲠在喉的事物,即为成长。
香菜原产于物种繁荣的地中海沿岸,汉朝时跟着张骞传入中国,称“胡荽”。中国明代学者屠本畯的《芫荽》诗云:“相彼芫荽,化胡携来”,便指此事。后来因五胡十六国石勒称帝,他是胡人,忌讳“胡”字,胡荽变“香荽”,后有元朝忽思慧《饮膳正要》改成“芫荽”。
“胡荽”之名,带着异域的神秘,自踏入中原大地,便在饮食的江湖中掀起波澜。“香菜”之称,又添了几分雅致与清新,仿佛其香可入诗画。而“芫荽”二字,更是别有韵味,读来唇齿生香。正如古人云:“名者,实之宾也。”无论何名,芫荽之味,始终独特而迷人。
莎士比亚说:“玫瑰不叫玫瑰,芬芳如故。”此言套在芫荽身上倒也通用,不拘何名,还是那个味儿。今日的芫荽大概已经没有“胡味”了,反倒是满满的芫荽,撒在热腾腾的卤味、面线或羹汤上,料理的灵魂瞬间醒转;当然也充盈着满满的人情味,昔日菜贩随手附赠一把香菜,曾是多少妇女的小确幸,如今菜价飙涨,仿佛都能闻到哀怨的味道了。
想那芫荽,于厨房之中,是那画龙点睛之笔。母亲常以其为佐料,为平淡的饭菜增添别样风味。她会将新鲜的芫荽洗净,细细切碎,撒在刚出锅的热汤面上。那芫荽碎如绿宝石般点缀在白色的面条与清澈的汤中,香气随着热气袅袅升腾,令人垂涎欲滴。有时,母亲会将芫荽与豆腐丝凉拌,淋上香油、醋和少许的盐,简单的食材在芫荽的加持下,变得清爽可口。又或是在炖鱼时,加入一把芫荽,去腥提鲜,让那鱼肉更加鲜美。
古人相信说秽语有助香菜成长,但宋朝的李退夫是个读书人,撒播种子时,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只好摇头晃脑地说:“夫妇之道,人伦之性。”后来客人来访,他让儿子接手,谁知年轻人更觉碍口,只好边撒边说:“刚刚我爹讲过啦!刚刚我爹讲过啦!”在士人圈引为笑谈,从此只要大家聚在一起闲聊八卦,就会打趣说:“今日宜撒芫荽一巡。”这则趣闻,为芫荽的生长增添了几分神秘与诙谐。
芫荽是否爱听脏话,我不清楚,但确信它不会在意那些揣测,毕竟它始终有被讨厌的勇气;而那别致如羽毛的叶片,以及开起来像把蕾丝伞的花,是芫荽总被人忽略的美好,更是它抵御中伤的方式——从容且优雅。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芫荽亦是如此,它不以他人的喜好而改变自身,默默生长,散发芬芳。其叶之翠绿,其花之淡雅,自成一道风景。在岁月的长河中,芫荽历经变迁,名称更迭,却始终在餐桌上占据一席之地,为人们的味蕾带来独特的体验。
“青青芫荽,悠悠我心。”它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生活的滋味。在这纷繁喧嚣的世界里,芫荽以其独特的存在,告诉我们,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坚守自我,绽放光芒,便是最美的姿态。
黄宗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