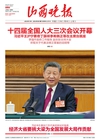起笔精彩 收笔饱满
我总想起几年前那只摔碎的笔洗。分明前夜还在案头盛着半盏月光,转眼就成了满地碎渣。那天,我蹲在狼藉里捡拾残片,指尖被割破的瞬间突然明白:有些坚持,是有代价的。
初执笔时爱追风骨。把《兰亭序》里“惠风和畅”四个字临得剑拔弩张,墨汁溅得满墙星点,以为力透纸背便是气魄。直到发现竖画总在末端发虚,像春苗突遭倒寒,蔫头耷脑地戳在纸上。那日撕了三十张毛边纸,墨团在废纸篓里冷笑,我才懂得王羲之说的“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原是教人先驯服骨子里的毛躁。
转机藏在某个周末。我见母亲用旧报纸包砚台防尘,泛黄的纸张间突然抖落半张烟壳纸。正面印着褪色的“大前门”,背面是歪斜的毛笔字:“2008年除夕,日课三百字未辍”。墨迹洇染如苔痕,除夕的红纸碎屑还黏在边角。忽然明白,真正的功夫不在雪白的宣纸上,而在这些被柴米油盐腌透的边角料里。
从此案头便长出了自耕的田垄。三伏天临《多宝塔》,汗珠滚进砚池,竟调出意外的苍润;数九寒天写《灵飞经》,冻僵的手指在热水袋上烙出红痕,却让笔尖多了三分峭拔。最难忘某个暴雨夜,狂草写到“惊蛇入草”四字时突然停电,摸黑挥毫竟得了天然趣。有光时再看那歪斜墨迹,恍惚是怀素醉后踢翻的砚台,泼出半卷风雨……
某个写《灵飞经》的子夜,蝇头小楷突然在灯下活过来,撇捺如燕尾裁开宣纸,恍惚看见敦煌抄经生在烛火中俯身,沙漏里的细沙正与他笔尖的墨滴同步坠落。原来千年光阴从未断绝,都在横竖撇捺间流转。
七年光阴在碑帖间显影。春天用露水醒笔,秋天借月光晒纸,小满那日终于悟透“屋漏痕”的真意——哪有什么玄妙技法,不过是让笔墨顺着时光的裂缝自然生长。前几日重写《兰亭序》,往昔滞涩的“之”字竟生出流水之势。收笔时暮色恰染透窗纸,最后一捺的飞白里凝着七年的晨昏……忽然觉得,所谓功夫,就是将浮躁驯成泰然,把慌乱熬成从容。
今晨翻出旧作,风掀动纸页如白鸽振翅。七年前歪斜的“永”字躺在最底层,上方是去年获奖的《赤壁赋》。阳光透过云母笺,照见每一道颤抖的笔触如何生长成筋骨,每一团懊恼的墨渍怎样沉淀为底气。
□章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