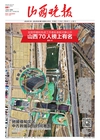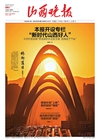漫谈“家”——一位大学教师笔下的家文化
古代家庭大小之辩
在古代,累世同居的大家庭经常受到朝廷的提倡和旌表,相关事迹在正史、地方志等文献中并不鲜见。据称,唐代郓州人张公艺出生于北齐,历经北周、隋朝、唐朝,九代同居,全家九百余口,始终能和睦相处,成为古代治家的典范。浙江浦江郑氏一门从南宋至明代,合食义居达十五世,鼎盛时全家三千余人,明太祖赐称“江南第一家”。
上述两则事例,反映了古代累世同居的大家庭的基本形态。在传统认知当中,古代是大家庭占主流,近代以后小家庭才逐渐流行。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综合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秦汉时期的家庭以小型核心家庭为主,平均家庭人口一般不超过五口,被称为“汉型家庭”。这一特征与秦国商鞅变法时的“分户令”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小型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仍占主体,但规模较大、结构复杂的多代同居家庭在上流社会较多出现,家庭与同族宗亲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隋唐时期,平均家庭人口规模比秦汉时期有了提高,八口之家相对常见。由于唐律对父祖在世而分家的行为予以重罚,已婚兄弟同居共财现象较为普遍,被称为“唐型家庭”。但新的研究表明,唐代中后期核心家庭仍然占主流。宋元时期的家庭通常是三代五口之家,有学者称之为“宋型家庭”。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对父祖在世而分家的行为处罚力度减弱,客观上默许了分家的合理性,这使得平均家庭人口规模趋小。不过,对这一时期家庭形态的判断,争议较大,一些区域个案研究的结果甚至相互抵牾。
由此可知,秦汉至明清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并不占主体,主流价值与历史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其实,不仅家庭的形态随社会变迁而不断演变,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家庭的类型也各有特点。因为全国各地的所有家庭不可能按相同步调、等宽步幅去变化和发展。南宋赵鼎在家训中要求子子孙孙不可分割财产,世世代代保持一户。而东晋陶渊明虽在《与诸子疏》中以大家庭事例教育子女和睦相处,但也说“虽不能尔,至心尚之”,并未强制后人合家共居。
其实,古代社会对大家庭的褒扬和期待,归根到底是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卑有序、一门邕睦的向往。其重点不在于家的形式,而在于家的内核。这一点,《袁氏世范》有比较集中而全面的论述。
大家庭的维系贵在“均”。为人父母者或偏爱长子、长孙,或偏爱幼子、幼孙。由于“憎爱之偏”,生活中衣服饮食、言语行为等方面,父母常厚待于偏爱之子,而薄待于所憎之子,由此导致受溺爱者日益骄横,受憎恶者心不能平。此种情绪日积月累,会造成兄弟之间的不和,甚至家道衰败。而为人子者,也应当知晓父母之爱,“长者宜少让,幼者宜自抑”,从而形成兄弟友于的最好状态。
大家庭的管理贵在“公”。兄弟子侄同居一处,人多事杂,众口难调,想要治理全家,贵在怀有一颗“公心”。即使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不可私藏金宝。若有一人处事不公,自私自利,总想多占多得,其他人定然心生不满,也就容易引起争端。而若“各怀公心,取于私则皆取于私,取于公则皆取于公”,众人都能分到公平的一份,哪怕这个数目很小,也能从根本上杜绝非议。
大家庭如能长久延续,固然是好,然“性不可以强合”,倘若难以合居,也不必勉强。袁采认为,“父必欲子之性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三观不合之人,断难共处一院。假如“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那么全家必然和睦协调,不会产生矛盾纠纷。在大家庭内“贤否相杂”的情况下,每人都需要有一颗宽容之心。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大家庭与小家庭同时存在,相向而行,相映成趣。大家庭的理想始终像一座灯塔,而实际的家庭形态则随着社会经济条件不断调适。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独特魅力。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