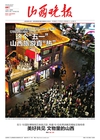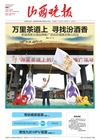邻里时光
我住在这条巷子里已有十年了。巷子不宽,两旁的砖房挤挤挨挨,墙皮剥落处露出青灰色的砖块,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每日清晨,阳光斜斜地穿过电线杆,在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对门住着王婆,七十多了,头发花白,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她每日早起,搬一把竹椅坐在门口,手里捏着一把蒲扇,眼睛却不住地往巷口张望。起初我不解其意,后来才知是在等她那个在城里做工的儿子。儿子每月回来一次,带些点心,王婆便笑得皱纹都舒展开来,将点心分给巷子里的孩子们。
隔壁是张师傅家,修自行车的。他的铺面就开在自家门前,终日叮叮当当。张师傅的手粗大黝黑,指甲缝里总嵌着黑乎乎的油渍,却能灵巧地将那些七零八落的零件拼凑成完整的车子。孩子们常围着他转,他便从兜里摸出几颗水果糖分给他们。他的妻子是个瘦小的女人,每到饭点便站在门口喊:“吃饭了!”声音尖细,能穿透半条巷子。
巷子尽头住着李老师,退休的小学教员。他戴一副圆框眼镜,走路时总微微驼背,像是在寻找什么遗失的东西。李老师家门口种了几盆花,他常常蹲在那里侍弄,偶尔抬头与路过的人点头致意。夏日傍晚,他会在门前摆一张小桌,泡一壶茶,慢慢地喝。有时我会过去坐坐,他便讲些旧事,讲到高兴时,眼睛在镜片后闪闪发亮。
我们这条巷子的人,见面不过点头问好,闲话家常。下雨了,会互相提醒收衣服;谁家做了好吃的,也会分给邻居尝尝。最热闹的是逢年过节或者嫁娶那几日。大人们一起忙活着,孩子们则在巷子里跑来跑去。大家都没有待在家里,谁家有需要帮忙的喊一嗓子即可,几乎都不用出门,邻居们就一呼百应了。
记得去年冬天,王婆感冒发烧,是张师傅蹬着三轮车送她去的医院。李老师知道了,每天熬了粥送去。我也跟着去探望过两回,王婆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却还惦记着门口的花该浇水了。
平日里,巷子安静得很。只有清晨卖豆腐的吆喝声,午后收废品的铃铛声,傍晚放学孩子们的嬉闹声,构成了这里最寻常的声响。有时我站在窗前,看着夕阳将巷子染成金色,王婆仍坐在门口,张师傅在修车,李老师在浇花,便觉得时光在这里走得很慢,很轻。
如今城里高楼林立,这样的小巷越来越少了。人们住进了电梯公寓,关上门,谁也不认识谁。我有时想,所谓邻里之情,不过是在这方寸之间,彼此记得对方的存在,在需要时伸一伸手,在平常日子里点一点头。
这便够了。
□周淮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