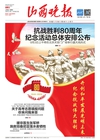我的第一份暑期工是赶猪进城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乡中学读书时,父亲在乡食品站当站长。那时,刚改革开放,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增,粮食生产也大幅增加,家家都有了余粮,农家人便开始用余粮来养猪。当时,农家出售自养猪需要到设在乡政府的食品站。
记忆中,父亲所在的食品站主要工作就是收购农家饲养的生猪。父亲经常和几个同事步行着去附近的村子里收购生猪,每当收购到百十来头猪后,便集中送往县城的食品公司。我们乡的食品站距离县食品公司有25里,一般收购回来的生猪是由食品公司的货运卡车拉走,但有时食品公司的货运卡车去了其他乡镇,父亲他们就需要找人把收购回来的生猪赶到县城的食品公司。每次赶运生猪,都需从村子里雇用几个农民帮忙,工钱是每人2元。那时的2元钱在村民眼里,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有一次,正好是礼拜天,食品站一大早就在做着往县城赶猪的准备。那天,我正想去县城书店买几本书,便和父亲嗫嚅着说:“我想进城买几本书,今天跟着你们一起进城吧。”父亲高兴地说:“也好,今天正好还缺一个赶猪的,你也算一个,顺顺当当把猪赶进城,也给你发2元钱。”
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的猪真不好赶。从乡食品站到县城的那条路两旁全是庄稼地,赶猪上路后,一百多头大肥猪哼哼唧唧着挤成一团。我和父亲与另外雇来的两名村民分别守在猪队伍的前头、后面和左右两旁,前面的人给猪带路,左右两旁的人防止猪跑庄稼地里,后面的人防止猪掉队丢失。就在快到县城的一段路上,猪群前面开来一辆卡车,一声喇叭响后,像在猪群里扔进了一枚爆竹,受惊的猪一下就炸了窝,慌乱地四散奔逃。有许多猪窜进了路边的庄稼地,我们几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惊魂不定的猪收拢在一起。待小心翼翼地赶着猪群穿过热闹的县城街头,走进县食品公司交猪点数时,才发现少了一头。几个人顾不上去县城做其他事,连忙原路返回,在猪受惊的那片地方细细搜寻起来。最后,我在一块玉米地里发现了那头走失的猪,它正卧在庄稼地里呼哧呼哧喘粗气。几个人再次把那头猪赶回食品公司,才算交了差。我拿着赶猪挣来的2元钱,跑到书店,买了几本心爱的书。
利用休息时间,我还参与过几次赶猪,前前后后一共挣了10多元钱,全部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书,算是我第一次暑期打工吧。
第二次“打工”赚钱,是在父亲做监工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
随着企业流程的精简,食品公司为省去一道手续,要求父亲他们把收购回来的生猪就地屠宰冷冻,然后食品公司派车来调运猪肉。这就需要重新建设生猪圈舍和冷库,于是,父亲向村子里申请了一块地,开始建新食品站。
那年,我正好初三毕业,在家里等待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父亲便把我“抓差”到工地上当了一名抱砖瓦、递灰斗的小工。每天早上7点上工,一直干到晚上8点多收工,每天的工资是2元钱。父亲天天在工地上当监工,从早到晚在工地上转悠,偶尔会帮我抬抬灰斗,替我擦擦脸上流下来的汗水。这样,我咬着牙整整在工地上干了一个月,直到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我带着自己凭汗水挣来的60元钱,到校缴纳了一学期的学费、书费和一个月的伙食费。
学生时代的两次“打工”经历,让我明白了挣钱的不容易,也懂得了大人养家的辛苦。从那时起,我养成了过日子勤俭节约,量力而行的好习惯。
白建平(岢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