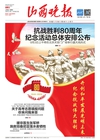夏收打场
1975年夏天,我在太原市南郊区小店公社红寺村插队。到了6月中下旬,小麦成熟了,我们立即投入了“三夏会战”,那是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日子,白天下地收割,晚上还要夜战打场,一天四出勤。
夏收就是龙口夺粮,和雨天赛跑,若田里的小麦被雨淋了,就会生芽减产。天刚泛白,村里的喇叭就喊上了:“社员同志们,下地割麦子了!下地割麦子了……”在喇叭的吆喝声中,我们到了地头,每人三垄,割到地头,把麦子打成捆就收工。吃过早饭,队长就在门口又催着下地收小麦。烈日炎炎下,衣裳湿了干,干了湿,手和脖子上常被麦芒划出道道血痕。中午食堂送饭到地头,直到日薄西山才收工。晚饭后,我们还要打场到深夜。
田里的庄稼收割后,牛车、马车、拖拉机把小麦拉到平坦宽敞的打谷场。小麦一卸车,就要摊开晾晒,让麦穗干透,便于打场时麦粒脱落、储存,避免粮食在保管中发霉变质。麦穗干透了,开始用碌碡(圆柱形的石滚子)碾压。村民一手牵着驴或者骡子的缰绳,一手拿着鞭子赶牲口。牲口后面拉个碌碡,转着圈碾压麦穗。牵牲口的活计需要有经验的“老把式”干,我们拿着木杈,把碌碡碾过的麦穗叉起来,翻腾一下,让小麦壳里松动了的麦粒脱落下来,一般要碾好几遍。最后,把麦秸堆到场边,摞成一座高高的圆圆的麦秸垛。
经过碌碡碾压后,还有少数麦粒没脱落,就要用连枷再拍打,直至小麦全部出壳。连枷是一种古老的农具,把几根细木棍有规则地编成一排,形成长条木片,然后与一根木杆相连,连接处必须是可以活动的。挥动木杆时,木片上下轮转,击打麦穗,就能让麦粒脱落。有时十几个村民排成一溜儿,一起挥动连枷,上下翻飞,发出整齐的“啪、啪、啪”声,甚为壮观。
叉走麦秸后,再用木刮子、木锹把小麦聚成堆,用簸箕将粮食倒入扇车上的漏斗中过风,吹去小麦里的皮壳杂质,分离出砂石土粒,小麦经过这么一收拾,就变得干干净净了。
摇扇车是打场中的技术活,操作的老农由上往下有节奏地拨动铁质的手柄,摇动风扇,利用手柄转动的惯性,人们从上往下给它加力,转几圈用手拨一次,稍不协调,就会打伤手或胳膊,轻则淤青,重则骨折。我曾试着摇了一会儿扇车,速度跟不上,也不能保证转速均匀,只能算是体验了一把,也明白了为啥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干这件事。扇车速度过慢风力小,杂质去不净,风力过大,会把麦粒也吹到杂质里,力度要掌握得“恰到火候”,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掌握的。
我们晚上打完场收工就到半夜了,麦收期间有上夜班的社员,他们还要继续忙碌。
回想当时收工后,回村的路上月光皎洁、蛙鸣虫叫,累并快乐着。
梁建军(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