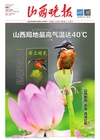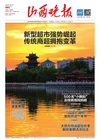供销社曾是全村人最爱去的地方
我的家乡应县水磨村供销社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位于村子当街,坐西朝东,旁边是观音阁和村戏台。供销社的南面一间房住人,北面一间是库房,中间是柜台,建筑面积有300多平方米。
当年供销社的商品齐全,大到村民生产需要的农具铁具,小到生活必需品样样都有,整齐的货架上琳琅满目。在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的商品基本满足了全村人的购买需求,极大地方便了全村的父老乡亲。那时的东西,货真价实,也没有假冒伪劣之说,也不需要搞价还价。
当时能在供销社当售货员可是个让人羡慕的好职业,是人们所谓的“铁饭碗”,当年村里人把售货员又称为“站栏柜”。“站栏柜”的人能享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供销社进来什么紧缺商品,有什么减价处理商品,都能优先买到。那时,在我们水磨村供销社站过栏柜的有薛家营村的石英峰、刘霍庄村的薛日明、韩家坊村的曹金友和韩成、石桥村的白仲文,本村的刘善、王甫、刘艿萍、刘一峰等人。当年“站栏柜”的售货员对人态度都很好,不论老乡们买不买东西都会笑脸相迎,热情待客。
当年“站栏柜”的人有一项技能,那就是必须会打算盘、会算账,因为供销社每个月的月底要关门盘点。存货多少、进货多少、剩货多少、卖了多少钱,必须货、账、钱相符。除了会算账,会称物、会包装、会扯布也是“站栏柜”的一项基本功。过去的商品一般都没有包装,像食盐、碱面、苏打、花椒、大料、干姜、白矾、白黑糖、饼干等都是散装的,过去没有电子秤,大多数用的是盘子秤,熟练的售货员用盘子秤下去一铲一搲一称,基本与顾客所要的分量八九不离十。称好商品后倒在一张预先裁好的一块正方形包装纸上,这种包装纸是当时供销社特有的较粗糙的灰褐色纸张,根据购买商品量,裁成大小不同的正方形,专门用于包装散货商品。
那时供销社的商品都可以零卖,一分钱可以买一块糖蛋蛋,二分钱可以买一支香烟,俗称“拔零根”。记得当年供销社卖的卷烟有河北张家口卷烟厂出品的“官厅”烟、“迎宾”烟等,人们喝的酒主要是应县酒厂酿造的“应州白”,浑源县酒厂生产的六十五度的老白干。酱油、陈醋也是散装散卖,没有包装,所以在供销社的地上放着好几个大缸,酱、醋分别装在大缸内,用一斤、半斤专用的塑料壶称打。
因为供销社里的副食品齐全,所以农闲季节或天阴下雨时,村里的青年人常去供销社买点午餐罐头,称点花生米、猪头肉,再打上二两散装白酒,煮几个鸡蛋,一起打平伙儿聚餐。
供销社是村子里最红火、最热闹的地方,除了购买商品,人们有事没事,不管买不买东西,都想去供销社凑凑热闹,听听国家大事、邻村的家长里短,看看新进了什么商品。特别是农闲时节,人们聚集在供销社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拉家常、翻腾闲话。供销社最忙的时候是每年的腊月和正月,置办年货的、购买礼品走亲戚的出出进进、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那时候供销社里有很多商品是凭票供应的,没有票有钱也买不到。我小时候看到供销社栏柜里摆放的水果罐头、面包等吃喝就会不由得流口水,这些东西只有头疼脑热的时候,母亲才会给买一瓶水果罐头。也奇怪,那时候吃完罐头,病就好了,特别见效。
供销社除了销售商品,还收购畜禽、药材及废品。当年家里把猪毛、骨头、烂铜、烂铁、烂鞋底等积攒起来,拿到供销社换钱。鸡蛋是换取零花钱最多的农产品,平时用的油盐酱醋基本上都是拿几个鸡蛋到供销社换购的,所以当时村里家家户户养鸡,下的鸡蛋很少舍得吃,都卖给了供销社。过去供销社还收购活兔,每个星期定时收购一次。记得当年父亲在自家院落里盖了一排低矮的兔窝,养了三十多只兔子。每天大哥、二哥放学后,就到村南庄稼地埂割草喂兔子。兔子繁殖快,基本一个月一窝,经过一家人精心喂养,长到三斤以上就可以出售了。每到出售兔子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带领大哥、二哥便到供销社取回装兔子的铁笼子,第二天用小平车推到供销社出售,养兔卖兔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除了贴补家庭生活开销外,还能给我们弟兄三个交学费、书本费。
由于我们村子大,村民购买力强,相邻的臧寨公社供销社每隔三五天就用皮车给我们村供销社送一次货,有时候单独拉一种商品。供销社的商品都是明码标价,无需讨价还价,不存在上当受骗。不像现在的商场,永远捉摸不透商品的价格到底是多少,买什么商品都得搞价、砍价,生怕上当。还有什么活动呀、打折呀、促销呀,五花八门、花样百出。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市场的逐渐放开,我们村里有经营头脑的村民陆续开了小卖部,不久就达到了七八家,再加上我们村交通便利,进城购物也十分方便,村供销社的经营很快就受到了冲击,日益衰落,被迫关闭。如今村供销社的房屋仍在,只是再无往日繁华,每次路过都忍不住唏嘘,曾经的热闹恍如昨日。
王汉平(应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