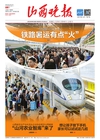澄城水盆
渭北高原的晨雾还未散尽,澄城老街的青石板大街水盆羊肉店的木门“吱呀”推开,热气裹着肉香涌出,与初升的朝阳撞个满怀。
澄城水盆的渊源可追溯至周代“羔羊羹”。《礼记·内则》记载的“牛修、羊修”,便是将肉切块炖煮的雏形。唐时渭北为京畿要地,戍边的将士以陶盆盛羊肉汤暖身,水盆之名由此而来。明清商贾往来,将这种便携美食带至四方,也在澄城这片黄土上生根发芽,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味。
我走进老城街一家木匾斑驳的水盆铺子,室内八仙桌与条凳仍保持着百年前的样式。掌柜张师傅家族五代熬汤,他抚着祖传的紫铜锅说:“这口百余岁的老铜锅,是水盆汤头的魂。”墙壁上泛黄的老照片里,戴瓜皮帽的食客捧着粗瓷大碗,与今日捧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形成奇妙重叠,变的是器皿,不变的是对一碗好汤的虔诚。
澄城水盆的精髓,在于对食材的极致尊重。羊肉必选渭北平原的关中山羊,这种吃着苜蓿草、喝着矿泉水,每日健步几十里长大的羊,肉质细嫩、筋道而无膻味。
汤骨的挑选近乎严苛。只取羊后腿骨与脊椎骨,敲断后露出骨髓,在清水中浸泡六小时去除血水。佐料是二十余味中药的协奏曲:小茴香打头阵,草果、良姜紧随其后,最后点一撮澄城特有的“十三香”——这是祖辈在黄土里摸索出的黄金配比。
张师傅告诉我,凌晨三点,汤锅便开始点火咕嘟了。紫铜锅里,羊骨与老汤按三比一的比例下入,大火冲滚后撇去浮沫,转文火慢煨。这锅汤要熬足八小时才够格。其间,张师傅每隔半小时便要舀起汤汁观察。好的汤头应呈琥珀色,表面浮着层金黄的油膜,像凝固的阳光。
切肉是门视觉艺术。煮熟的羊肉自然冷却后,张师傅手持四寸尖刀,手腕轻抖便切出薄如纸张的肉片。肥瘦相间的“腰带肉”最受欢迎,就连盛汤的粗瓷碗,也有讲究,碗壁厚实能保温,碗口微敞便于散热。张师傅将肉片码在碗底,上面覆盖粗细均匀的“黄瓜条”。最后浇上滚烫的汤头,肉片在热汤中微微卷曲,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波浪。
吃水盆有套仪式感。先掰块月牙饼泡入汤中,待其吸饱汤汁变软,再夹起肉片蘸油泼辣子。第一口要喝原汤,让醇厚的滋味在舌尖化开;第二口加香菜葱花,品出清新层次;最后把饼泡透,就着糖蒜吃下,酸甜辣咸在口中炸开,那感觉,恍若听见了秦腔的激昂与信天游的悠长。
澄城人讲究“以汤养身”。羊肉性温,能驱散渭北高原的寒气;汤中的胶原蛋白是天然美容剂;而那二十余味中药,实则是古代医食同源的智慧结晶。老食客们会指着汤碗说:“这汤能去湿气,你看我这老寒腿,喝上三个月健步如飞。”
夕阳西下时,老街的水盆铺子汤锅里的热气升腾成云,裹挟着千年的烟火气,飘向渭北高原的尽头。
离开澄城时,张老板往我的行李箱里塞了几包真空包装的水盆羊肉。但真正懂行的知道,这汤要现喝现熬,就像乡愁总要沾着生养的泥土,带着成长的温度才动人。
这或许就是中国人饮食中最动人的模样——在一碗汤里,看见时间的厚度,尝出土地的温度,品出文化的深度!
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