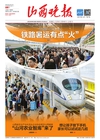我的学费
我是1961年生人,那个时候国家极度困难,我们家也家境贫穷,所以从小学到大学,我都在为学费而发愁。
我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年东山日头背到西山,也挣不了几毛钱,我上小学时,一年两三块钱的书费都交不起。我大伯父算是个生意人,在集市上卖菜籽,手头比较宽裕,父亲无奈之下就让我找伯父借,谁知一进伯父家门就遇到刚过门不久的堂嫂,把我一顿臭骂,赶了出去,我只好含泪而返。
后来我在临猗县艺术学校读书,学的是美术,一学期7元钱的学费交不起,父亲只好把家里唯一的一瓶食油卖了给我凑学费,可依然难以为继在县艺术学校的学习,我只好转学到本村的孙吉高中,这样可以省下生活费,又不至于辍学,但还是被15元的学费难住了。父亲看遍人间脸色,借到了7块钱,还有8块钱的缺口,怎么办?村里有些养猪的人家收干草,就是把草晒干,然后用铡刀切成一寸长的样子,一斤3分钱。6斤草才能晒出1斤干草,算一算,我要把这8元的学费凑齐,需要割多少斤草?1600余斤!那年暑假,我顶着烈日拼命割草,手磨出了茧,肩压出了泡,脸晒出了油,汗流成了河,但我无怨无悔。父亲从生产队的马房借来铡刀,我和父亲每天铡草,然后挑着卖给养猪的人家,如此坚持了足足一个暑期,终于凑够了那要命的15元学费。可以说,我的高中之门,是用父亲的乞求讨开的,是用我的镰刀割开的。
两年高中苦读,1980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高兴之余,又为学费发愁了。父亲依然是看遍人间脸色,低三下四,求爷爷拜奶奶,到处借钱。我的堂姐夫在荣河镇粮站当站长,是“吃皇粮”的人,又算是个官儿,父亲硬着头皮、低下长辈的身段,从孙吉村到荣河来回走了60里路去借钱,结果吃了闭门羹。最后还是靠乡情,邻里邻居的乡亲们恭喜我金榜题名,纷纷来家贺喜,有的送一毛钱,有的送两毛钱,有的送五毛钱,有的送一块钱,有的送两块钱,有的送五块钱……最多的是我们队的生产队长丁守义送了30块钱,就这样凑够了我入学的学费。
四年大学生活,我享受了国家头等助学金,但生活费依然是个问题。我二姐夫开砖窑,年过六旬的父亲就在姐夫的砖窑帮工,为我补贴生活费。最难忘的是每当我上学时,母亲总会拿出一个小手帕,里面裹着一些零碎钱,有1分、2分的,有5毛的,最大面值的就是1块钱,都是她捡破烂攒下的,母亲小心翼翼又郑重其事地交给我,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最拮据的时候,为了供我读书,父亲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连一只小板凳也未能幸免。我爱人回忆第一次到我家的印象:家里房屋没有正式的门,只有用纸糊的风门;没有人坐的地方,只能坐在炕沿上;没有煤炭,烧饭用柴火;没有餐桌,待客就是西瓜就馒头;有一间房顶上有个大窟窿,下雨就会落在屋里面……真是穷得彻底!
任何的艰难困苦,都动摇不了父亲让我求学的坚定意志,他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但他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我小时候,父亲特别羡慕民办教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当上一名民办教师。如父所愿,我不仅当上了正儿八经的人民教师,而且还成为了深圳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现下,如果父亲知道我研究的“语文课堂立体教学策略体系”荣获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如果父亲知道我正在全国各个革命老区义务送教,推广自己的教学成果,收获无数掌声,他应该会笑得合不拢嘴……
□孙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