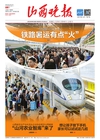闲话古代致仕年龄
古时通过科考,加入公务员队伍,“吃皇粮”叫入仕。年老退休,则叫致仕。早在西汉时由戴圣所编的《礼记·曲礼》上就写道:“大夫七十而致仕。”《春秋公羊传》亦称“退而致仕”,注释则说“致仕,还禄位于君”。南朝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年),御史中丞沈渊表奏“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这是从国家法律层面上,对退休年限的最早规定。
按古时物质条件、医疗健康水平而论,人的寿命如同唐代诗人杜甫在《曲江二首》中所写“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此诗写于758年。由于一生困顿,颠沛流离,身体不佳,杜甫卒于770年,终年仅58岁。
诚如孔老夫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古代,即便唐、宋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人生要活到七十”,稀矣。
虽说唐代诗人贺知章高寿86岁;宋代曾成功研制水运仪象台的苏颂寿高81岁,可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多乎哉,不多也!
以唐朝为例,人的平均寿命,有研究结论:唐代人平均寿命约为59.3岁(主要指贵族),平民因饥荒、赋役和医疗落后,整体寿命可能更低(约25-30岁)。即便官员阶层,寿数超过70岁的也是少数。
那么“七十而致仕”的规定是不是有点乱弹琴?
人的寿命,绝非像订指标,可以高一点儿,可以跳一跳。换句话说,既然致仕拿一份退休金,足可安享晚年,是一项国家福利,至少应该从实际出发,从人均寿命长短的实情出发,来确定退休的年龄才合适,将标准定为70岁,那么多“英年早逝”的人岂不是难以享受这一政策红利?
宋朝四大名臣之一寇准,病逝于被贬谪的雷州,终年62岁;范仲淹在转任颍州(今安徽阜阳)途中病死,终年64岁;包拯终年64岁;李纲死在福州的任上,终年58岁……
当然,未达退休年龄者,如唐朝则规定“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意即身有伤病,不宜再继续上班,可退休请俸;明朝亦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勒令退休。据介绍,明、清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京官叫“京察”,地官叫“大计”。如有德不称职、才力不及者,以及浮躁浅陋者,都要勒令致仕。
不过,对于政府要官来说,请辞,致仕并非易事。宋代名臣欧阳修一生仕途三次遭贬,以致心灰意懒,遂于61岁那年申请早退。可直到65岁,递了第七次申请才获准,到安徽颍州养老。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仅过了一年惬意的退休生活,66岁时,欧阳修便病逝了。
欧阳修死后,其子欧阳发撰写《先公事迹》时,对其多次申请早退的事情十分赞赏,认为父亲急流勇退,风格高尚,“近古数百年所未尝有”。不过,这只是自夸的话罢了。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宋仁宗时的宰相韩亿及其子韩绛,均曾提前申请退休(韩绛59岁即申请致仕)。王安石56岁时即辞去相位,申请退休;一年后被宋神宗重新起用,58岁时再次辞去相位做闲官,60岁时辞去一切职务,正式宣告退休,65岁时,去世。
其实,古代官员“请求”提前退休,在我看来虽可称高风亮节,更多的原因则基于官场环境不佳,或已受到皇上“冷眼”,产生了职业倦怠感;再如新官上任,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再被重用;更多的则因为健康的原因。古代在朝为官,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官员们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身心俱疲,再加上动辄被贬,去京三万里,不是高寒就是瘴气,身子骨经不起如此折腾。比如,永贞革新失败后,与刘禹锡同时被贬谪的柳宗元,就忧愤而死,年仅47岁。
由于决策缺乏民主性、科学性,导致古代致仕年龄与人伦情理和社会现实严重背离。至少说明,这一退休政策有悖人本关怀和人文情怀。
□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