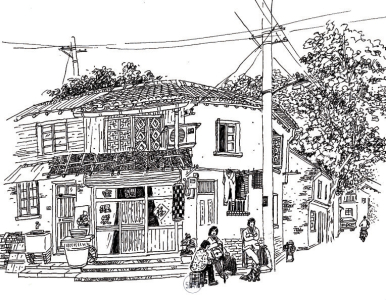在思绪里沉吟
李文晓
一年三回重相逢,
轻烟袅袅上天庭。
人间天上共神伤,
故人入梦话别情。
——题记
又见寒风起,又是“十月一”。又到了一年一度为故去亲人送寒衣的时节。母亲之前就多次打电话,再三叮嘱,“十月一”别忘了回家给先人“烧寒衣”。几次回家,离那日子还远,母亲就和我掰着指头算,今儿个初几了?再过多少天就是某某节了?照例还是叮咛个不停。九十多岁的母亲,别的日子都淡忘了,唯独三月里的“清明节”、七月里的“鬼节”、十月里的“寒衣节”从来不曾忘记,反倒是记得越来越牢固了。交待起来详尽而具体,一点也不含糊。对故人的思念,总是和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紧密相连,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便收不住口。
故乡的朝阳,总是从东面的崖畔升起。天光照亮了一蓬蓬枣刺,随后便染红窑洞窗户上的白纸。父亲已经挑满了水缸,水担“吱吱扭扭”的声音,和着他的咳嗽声,把天叫亮,把我们也都催促起来。朝霞满天的时候,父亲扛着锄头的剪影渐渐淡去,消失在广阔无垠的田野里。故乡的落日,又从西边的沟壑缓缓坠下。夕阳里,我看见他疲惫的身影朝我走来。肩上的老镢头,把他武装成打靶归来的战士,步履显得沉重,却也不乏坚定。瑰丽的晚霞,把田野和小村披上金灿灿的纱裙,大地流光溢彩。落日里父亲矮小的身子,瞬间变成一个金光闪闪的巨大影像,放射出道道光芒。晚霞不再是残阳如血的悲壮,也没有日暮途穷的悲凉,更没有夕阳西下的哀伤,只有生命回归原点的淡定与平常。回味这情景,让我咀嚼出了生命的酸辛与短暂,人世的无奈和沮丧。故乡的月儿,不论阴晴圆缺,总在瓦蓝的夜空挂着。月光下,父亲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修理着镢头和铁锨,那是他不能出故障的宝贝,绝不允许它松动、生锈。而在漆黑的夜间摸索着纺线的外婆,怎能舍弃明月当头的好时光,“嗡嗡嗡“的纺线声,直把月亮送到西沉。我在外公讲了多少遍的“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里,迷迷糊糊进入梦乡。“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人世沧桑,循环往复。冷辉轻泻一地银,寒意侵人夜入眠。静谧孤独的小村,这时也进入了梦乡。我对故乡所有的记忆,如同村前的池塘,看也看不够;恰如路旁的垂柳,数也数不清。那些在小村所发生过的事情,都随着阵阵轻风飘向远方,唯有留在心里的人,凝聚成坚韧而长久的丰碑。
故去的那些人,在这个聚会的季节,从各个地方奔来,汇集到他们曾经的故乡,寻找他们曾经牵挂着的那些人。他们也许凭着记忆,走在惯常的路上,也许,什么都不需要,他们有的是神奇的法术,可以轻松自如地跨过道道峻岭,越过重重迷雾,故地重游。他们目之所及,或山野仍旧缕缕微光,或小村依然涂满苍凉,只是影影绰绰的人群改变了行装,变得不曾相识。那都市中的高楼大厦挤满天空,灯光火影,鳞次栉比。街面上的帅哥靓妹,衣着时尚,行走其间,记忆中搜索不到过往。乡音似犹在耳,山川早已变了模样。他们该用怎样的眼睛,重新审视乡村的一草一木,重新考量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烧一炷高香,用祷告和他们建立沟通渠道,似乎显得力不从心。只能借助神力把世界重新丈量,用智慧架起生命和心灵的桥梁。夜风乍起,轻轻地吹拂着。街巷燃起一团团火堆,那火焰舞蹈似的跳跃着、闪烁着、流动着,风吹起带着火星的纸灰,向着深邃的夜空飘去。夜风吹旺了火焰,焚化了纸做的衣被,带去了凡间儿女至诚至真的心愿。而夜风却吹不走留恋和遗憾,吹不尽牵挂和思念。一年又一年,又见寒风起。风,刮不走哀怨;雨,淋不透愁绪;雪,化不尽忧伤。晨光带不来故人归,夕阳染不红离人愁,明月更难圆人神共有的幻梦。纵然我投入火中,化为灰烬,腾云驾雾,我的魂魄也要和故人结伴,萦绕在这片熟悉而又可爱的土地上,伴着朝阳升起,陪着夕阳落下,徜徉晴空,沐浴阳光,和风动,同雨下,随霜落,共雪飞,飘荡在故乡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永远……
(作者单位:平陆县交通运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