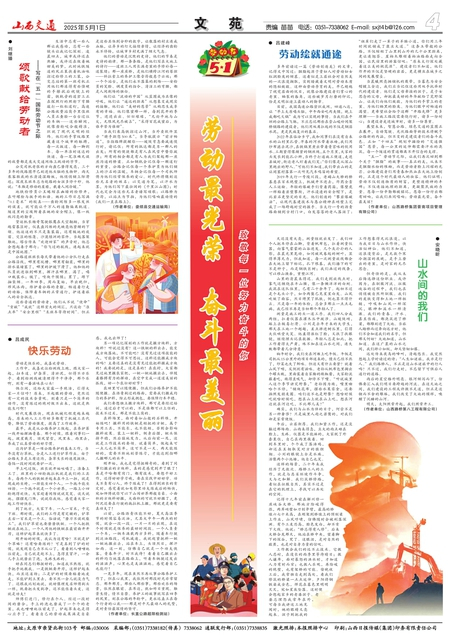颂歌献给劳动者
——写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群让我感动,总有一些镜头让我记忆深刻。凌晨四点,城市或许还在熟睡,或许还在做着她甜美的梦,此时地铁隧道的风正裹挟着机油味掠过检修工的工装,公交总站的第一班司机正用他们那冻得有些僵硬的手擦拭后视镜上的霜,铁轨旁的道岔工正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弯腰敲打一粒粒道钉,高速公路收费站岗亭里值班人员正查验一台台过往的车辆……这些瞬间,就像齿轮咬合般精准,织就了现代文明的经纬。他们的手掌纹路里藏着这个城市的脉搏,每一次扳道、每一脚刹车、每一单准时送达的快递、每一笔准确无误的收费都是庞大交通网络上跳动的字节。
公交司机老张的方向盘已磨得发亮,三十多年的线路图早已刻进他头脑的生物钟。雨天乘客鞋底的水渍浸湿踏板,他悄悄铺上防滑毯;深夜末班车总为赶路的女孩多停十秒。他说:“车厢是移动的屋檐,载着人间冷暖。”
地铁检修员小王蜷缩在幽暗的检修井,在听螺栓与扳手的私语。她的工作日志写满“0.1毫米”的较真——齿轮间隙多一根发丝的误差,就可能让千万人的通勤偏离轨道。隧道里的尘埃附着在她的安全帽上,像一枚枚闪亮的勋章。
货运机长杨哥驾驶银鹰在天空翱翔,当穿越雷暴区时,仪表盘闪烁的光映亮他紧绷的下颌。他运送的不只是集装箱,还有极地的疫苗、灾区的帐篷、沙漠绿洲的零件。当起落架触地,塔台传来“欢迎回家”的声音时,他总会想起妻子那句:“你飞过的航线,连起来就是中国地图。”
公路道班班长每天带着他的小分队行走在公路沿线,哪里有坑槽、哪里有翻浆,哪里的排水渠堵塞了,哪里的护坡下滑了,他和他的队员就进驻到哪里,挥汗在哪里。渴了,喝口瓶装水;饿了,啃块干馍馍;累了,蹲下抽袋烟。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早出晚归,栉风沐雨,维护着公路的身躯,畅通着行走的动脉,保障着车辆的正常通行,护送着旅人的安全抵达。
这些普通的劳动者,他们从不说“使命”“贡献”“成就”这样宏大的词汇,只谈论“准点率”“安全里程”“末班车等待时间”。但正是这些具体到分秒的数字,让散落的村庄连成血脉,让异乡的灯火接续亲情,让经济的齿轮永不停转,让城市乡村充满了烟火气息。
他们的劳动是沉默的史诗,他们的节奏是史诗的韵律。那一条条路,是他们写在大地上的诗行——道班工人用长满老茧的手修补每一道裂缝;那一座座桥,是他们横跨江河的琴弦——斜拉索上的养护工像音符般悬于云端;那一个个站台,是他们永不落幕的剧场——安检员的笑脸、调度员的指令、清洁工的弯腰,都是人间剧场的独白。
他们让“流动的中国”从蓝图成为具像的呼吸,他们让“遥远的距离”从想象变成现实的接触,他们让“美好的愿景”从构思生成享有的幸福。他们像蜜蜂一样,每到花开的季节,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无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当我们乘高铁掠过山河,当外卖软件显示“骑手距您500米”,当导航提示“前方畅通”,当指路牌提醒你——坡陡弯急要减速慢行时,请记住:所有的抵达都是另一群人的出发;所有的便捷都是有人在风雪中替你跋涉;所有的相会都是有人为我们架起那一座座沟通的桥梁。正如钢轨会记住每一颗道钉的重量,公路会记住每一个养护员为他们铺上的沙石的温暖,车辆会记住每一个司机师傅为他们经常保养的爱心。时代终将镌刻这些无名者的姓名:以交通为笔,以汗水为墨,为他们写下最壮阔的《千里江山图》;时代也定会为这些无名者谱写颂歌:以路桥为音符,以站点为节拍,为他们唱响最动情的《我们一直在路上》。
(刘继臻 作者单位:娄烦县交通运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