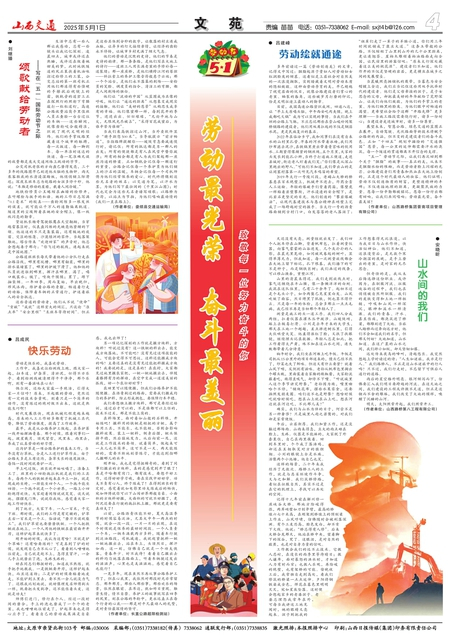山水间的我们
安晓昕
天还没有大亮,测量组就出发了。我们四个人把车停在山脚,背着帆布包,扛着测量仪器,向雾气蒙蒙的山谷进发。几个灰扑扑的人影,在晨光里晃动,如同被风卷起的树叶,显得单薄无力,但我知道,每一次测量放线都会在大地上留下标记,扎下根基,我们播下的可不是种子,而是钢铁巨树;我们画过的线条,可以移山换岳,重塑江河。
山里的清晨来得迟。我们走到放线点时,雾气还缠绕在半山腰,像一条懒洋洋的白蛇。我混在这队伍里,已有二十余年了。起初不过是个毛头小子,如今两鬓已见星星白发。山风吹皱了面容,烈日烤黑了肌肤,倒也算不得什么。只是每一年的体检,总会多那么一点点毛病,我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年轻人了。
测量是施工的头一道工序。我们四人分成两组,扛着仪器在灌木丛中跋涉。山坡陡峭,踩上去极易打滑。小刘是去年才来的大学生,那天在工地一个趔趄,差点摔进树丛里,引得大伙哄堂大笑。他羞得涨红了脸,又扶了扶眼镜,继续埋头记录数据。年轻人总是如此,把工作看得太严肃,殊不知在这山水之间,连失败都带着几分诗意。
晌午时分,我们坐在河滩上吃午饭。午饭是司机从15公里外的项目部送来的,馒头已经不热了,炒菜也失了鲜味。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就着山风下咽,反倒别有滋味。老孙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罐头瓶,里面装着自家腌的辣椒酱,大家轮流蘸着吃,辣得直吸气,却停不下嘴。“听说城里人这个季节讲究野餐,”老孙因为辣,嘴里嘶哈个不停,“铺块花布,摆些水果零食,还要拍照发朋友圈。咱们这不也是野餐?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想在山上就在山上吃,想在河边就在河边吃,不比那儿美?”
确实,我们与山水为伴的日子,何尝不是另一种奢侈?只是城里人趋之若鹜的,对我们却是家常便饭。
午后,云层渐厚。我们加紧工作,还是没躲过那场雨。山雨来得急,豆大的雨点砸在脸上,生疼。仪器是不能淋的,大家脱了外套裹住,自己在雨里挨着。回到车里时,个个成了落汤鸡,却还在互相取笑对方的狼狈相。小刘的眼镜上全是水珠,活像两个小池塘,他自己也笑。
这样的场景,二十年来我经历了无数次。路桥工人的工作,就是与恶劣环境作斗争,又与之和解。我们筑桥修路,看似在征服自然,其实不过是在它的肌理上,寻找可以共处的空间。
记得十几年前在解州修一座峡谷大桥。那地方险峻得很,两岸峭壁如刀削斧劈,最高的桥墩六七十米高,在刚架到桥墩上的预制梁上作业,山风呼啸,仿佛随时会被刮落深渊。有个工友恐高,脸色发白,却不肯下火线。他说:“桥总得有人修”。后来大桥合龙那天,他站在桥中央,望着脚下的深谷,哭了。这眼泪,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自身力量的惊叹。
工作教会我们的远不止技术。它教人忍耐,在漫长的雨季里等待晴日;教人谦卑,面对暴怒的洪水时,才知道人力有时而穷;也教人乐观,再险峻的绝壁,也有架桥的可能。傍晚收工后,我常独自走到高处,看我们修筑的桥梁一点点延伸。夕阳将钢铁染成金色,焊花在暮色里明明灭灭,宛如星辰坠落。这时便会想起家乡的老婆孩子。老婆总埋怨我常年在外,可每当我讲述工地见闻时,她的眼睛又亮起来。孩子则把我的工作想象得无比浪漫,以为我日日与山水作伴,快活似神仙。他们不知道,这浪漫背后,是无数个寒冷潮湿的夜晚,是手上磨出的老茧,是对家的无尽思念。
但奇怪的是,我从未后悔选择这份职业。或许因为,在驯服河流、征服峡谷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悄悄被自然所驯服。我们的皮肤变得和土地一样粗糙,呼吸和山风一样深沉,眼神和溪水一样清澈。我们的青春、汗水、甚至伤痛,都浇筑进了桥梁,都雕刻进了大地。当旅人踏桥而过奔向远方时,他们不会知道我们的名字,但那又何妨?大地知道,山水知道。在这广袤的山水之间,我们渺小如蚁,却又坚韧如藤。
远处传来夜鸟的啼叫,清越悠长。我突然想起上学时读过的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路桥人,不正是这山水逆旅中的行人吗?只不过,我们行走时,不忘留下可供后人通行的道路。
雨后的星空格外明亮。银河倾泻而下,仿佛要汇入我们明日要跨越的河流。在这天地之间,我们建设的工程或许微不足道,但正是这锲而不舍的雕琢,我们改变了大地的模样,唤醒了沉睡的山河。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我们照常开工。
(作者单位:山西路桥第八工程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