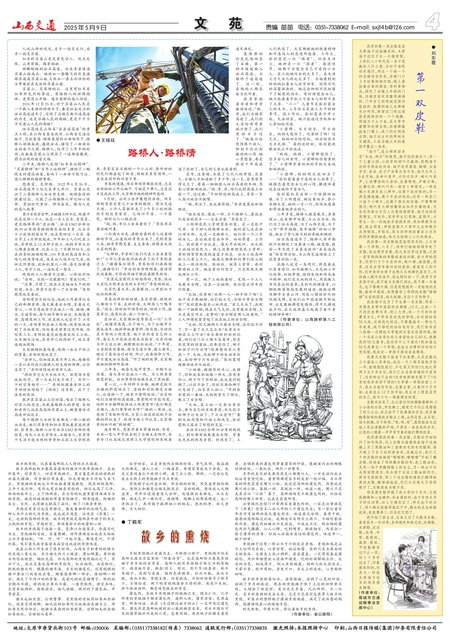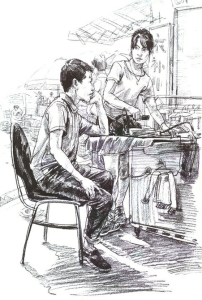第一双皮鞋
刘东霞
我穿的第一双皮鞋是在太原海子边地摊买的。太原海子边位于五一大楼西侧,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条不宽敞的人行小巷,当时不准机动车通行,两边一个挨一个的店铺密密匝匝,店铺门口上方扯根细钢丝绳,绳上悬挂着出售的服装、布料等物品,挡住了店铺上半部的门脸。店铺里面东西塞得满满的,门外自己的领地范围内能挂的、能摆的地儿也都被充分利用,除留出门的过道就是挨挨挤挤一个个地摊。那地方寸土寸金,是太原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店铺牌匾挂在门楣上,或门的左侧或右侧。海子边古朴的厚砖灰瓦建筑,只在店铺之间的缝隙中露出一些来。
“海子”,在古鲜卑语里是“水池、湖泊”的意思,海子边的南出口,有一个儿童公园,公园里的湖叫文瀛湖,我想海子边的名称由此而来。海子边里服装、鞋帽、五金百货、食品、电子产品等应有尽有,每天从早上9点开始,各种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喇叭叫卖声,汇成嘈杂的大杂烩,扯着喉咙,声嘶力竭,比赛似的。喇叭叫卖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推小车游走在人群中,这属于流动性的;另一种是摆地摊,属于半流动性的;还有一种是门口挂个小喇叭,这属于固定的店铺。不管哪种情况,喇叭里大肆喧嚷商品如何价廉物美,无非是用高分贝引人注意招徕顾客。海子边的东西便宜,可砍价,深受学生们青睐。星期天,大学生一伙一伙地在里面挑东西。我如果要买衣服,就去那里,学校星期天只供早九点和晚四点两顿饭,早饭后,我与同学相跟着坐公交车到那里精挑细选,每次总能购上心仪的物品。
我的第一双皮鞋就是在那里买的。上大学第一个学期,入冬了,同学们陆陆续续穿起了皮鞋,我也想穿皮鞋。我从来没穿过皮鞋,之前一直穿妈妈做的布鞋或者运动鞋。在大学校园里,同学们个个牛皮哄哄,喇叭裤,高跟鞋,烫发,这是女青年最时尚的装扮。爱美是人的天性,农村来的女孩子也想从头到脚武装自己,尽快融入城市洪流中。我也想时尚一下,我骨子里是保守的,我不敢与先锋们相比,我不要一头卷毛,也不要喇叭裤,但是我想拥有一双锃亮的皮鞋,最好半高跟,我想像穿上那样的皮鞋“蹬蹬蹬”走在校园里,抬头挺胸,自信十足的样子。
我在海子边买了平生第一双皮鞋,那是一双黑色系带半高跟的皮棉鞋,10元,比我一个月的伙食费还多。刚上大学,我一个月的伙食费是8元,开学爸爸送我到学校,走时留给我50元线,交待我吃好些,不要像高中一样吃几年咸菜,钱不够花的话给他写信。我们宿舍里八姐妹一次聊起大学报到后家长给留的钱,除一个当县公安局长的父亲留给女儿60元,就数我的50元最多,我还有什么不满足?我知道这50元我要花一个学期,包括生活费和所有的日用花销,我决定一学期不再向爸爸要钱。
我要买皮鞋只能省下伙食费,从买皮鞋这小火苗在心里串起,决定一天三顿买饭钱节俭一半。能填饱肚就行,少吃菜又何妨?比起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已生活在幸福的天堂里了,还有啥过不去的?还有啥困难克服不了?还有啥艰苦承受不得的?大学第一学期的前三个月,我生活虽然节俭,还算正常,从第四个月开始,也就是从12月份开始,我生活上简直是苛刻自己,每天只吃一顿最便宜的菜。
皮鞋买回来了,比以前任何的棉鞋都暖和。3公分高的后跟,穿在脚上,感觉它不仅让我增高了好几公分,而且给予了我满满的自信。我穿着黝黑锃亮的高跟皮鞋去上课,去阅览室,去买饭,抬头挺胸,目不斜视,“嗒,嗒,嗒”,高跟敲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不啻是一曲优美的音乐,让我的心随着一声声有节奏的敲打舞蹈起来。
我很爱惜我的第一双皮鞋,买鞋时仔细询问了如何保养,买上皮鞋后接着就在海子边地摊上买了黑鞋油和三面都有毛的专用鞋刷。每天晚上下自习回到宿舍里,洗漱过后,我们几个有皮鞋的姐妹就“唰唰唰、嚓嚓嚓”开始了擦皮鞋。我准备了两块擦皮鞋的布,在上鞋油前,先用一块干布擦掉鞋上的灰尘,另一块沾少许水再深度清洗。待水渍干后涂上鞋油刷均匀,再用毛刷刷亮。那三个没皮鞋的看我们擦得锃亮的皮鞋,酸溜溜地说,你们以后梳头不用照镜子了,皮鞋就能当镜子用。
那双黑皮鞋伴随了我大学四个冬天。它使我脚暖和心也暖和。毕业离校时,由于东西太多不好往回带,加上它确实旧了,样式也不时兴了,两只脚后跟磨得高低不平,脚尖的皮也粗糙起来,我犹豫再三,还是把它扔了。
我开始了新生活。后来又买了无数双皮鞋,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各种颜色和款式的,皮棉鞋、皮单鞋、皮凉鞋,低帮、中帮、高筒的,高跟、坡跟、平跟鞋都穿过不止一双,但三十多年过去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大一时在太原海子边买的那双黑皮棉鞋。
(作者单位:晋城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