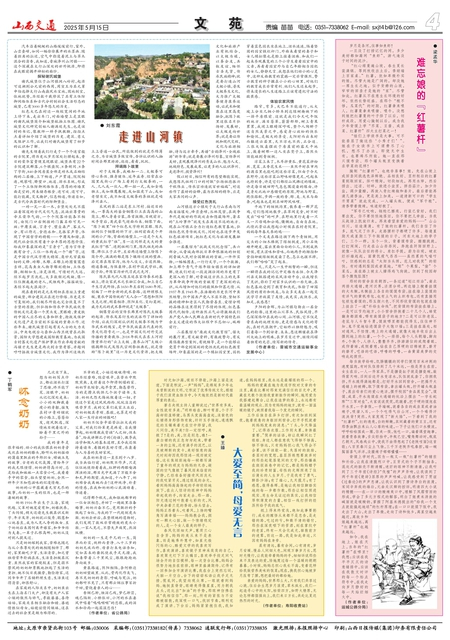难忘娘的“红薯杆”
梁孟华
岁月是条河,往事如鱼虾!
一旦没了打捞记忆的网,多少美好都如漏网“鱼虾”,游弋淹没于时间的泥沙。
“红心绿蔓遍山坡,春生夏长装满锅。等到秋收出土后,香甜端上百家桌。”红薯,犹如卑微朴实的娘,尽管大地是广阔的,却没她一席生长之地,似乎贫瘠的山坡,窄窄的田垄才是她的“家”。尽管如此,红薯从不在意生长环境的好坏,依然长势旺盛。在那个“粮不够,瓜菜代”的时期,红薯拿来喂人,红薯蔓拿来喂猪、喂牛,没想到娘把红薯蔓的叶子择了以后,切杆成段,用爱心腌制以后,成为我少年背馍上学“芥菜、豆酱、咸韭菜、红薯杆”四大主打菜之一!
“娃们上学读书是大事,可不能委屈了俺这些‘小秀才们’”。娘在子女读书上可谓费尽了心机,想尽了办法,即使无中生有,也要竭尽所能,她一直在那只馍布袋、那个罐头瓶里变换着求学菜的花样!
腌制“红薯杆”,也绝非易事!娘,先在山坡上或田垄间挑选色泽鲜艳、品相良好、茎杆粗壮的红薯蔓割取回家,择叶精淘,切段细冼,再用水焯,然后捞出、过凉、切碎,放进小盆里,拌些蒜汁,加少许盐,调少量醋,再放入青红辣椒和姜片,最后若能再滴几滴香油,更是美上加美,一道清新可口的“学生开胃菜”就此完成,一入罐头瓶,便成“军干粮”,清香带着微辣,味道好极了。
“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我们要出发,你不要悄悄地落泪,你不要把儿牵挂,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山山而川,征途漫漫,有了娘的红薯杆,我们自信了许多,底气足了许多,走路腰杆子都硬了许多。每逢星期天或星期三下午取馍的日子,河东大地上的学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背着馍布袋,蹦蹦跳跳,打打闹闹,行走在山山峁峁间,奔跑在阡陌田野上,就像一队队出征的将士,肩扛手提,蔚为壮观,破衣烂衫雄赳赳,面黄饥瘦气昂昂……虽然累的气喘吁吁,但感到的总是“太阳当头照,花儿对我笑”的轻快。有时遇到梨园或者菜地,“顺”个果梨,“偷”个菜瓜,虽在路上被主人撵得鸡飞狗跳,但到了校园却落个腹饱肚圆!
那时的宿舍坐东朝西,一条过道“划江而治”,南北两排大通铺,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两边墙上楔着挂馍的大木橛,木橛挂上各自的馍馍布袋。挂在墙上装馍的有洋气的黄帆布包,也有土气的土织布包,还有直接用包袱包着馍的,那五颜六色、不同形状背馍的包就在墙上挂出了一道“补给生命线”。把背馍的布袋挂在墙上,一是可以节约地方,小小宿舍挤挨着二十几个人,睡觉翻身都困难,哪有放馍袋子的地方?二是可以防老鼠,老鼠与人斗智斗勇,馍放哪里都能找得见,往往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馍袋子大饱口福;三是挂在高处,相对通风,不怕馊。晚上的大通铺,就像大地丰收后出土摆到地上的红薯,一个个,一排排,每个人头朝墙,脚向外,个挨个,人挤人,整整齐齐,挤游游似的或爬着眠,或仰着睡,或侧着憩,钻在自己厚硬的旧棉被里,磨牙的磨牙,呓语的呓语,呼噜的呼噜,一曲黄粱美梦的交响此起彼伏。
每当放学铃响,饥肠辘辘的同学们便用百米冲刺的速度猛跑,有时队伍排到了几十米远,一般是男生在前,女生在后,一人一件家具,不是搪瓷缸子就是搪瓷碗,敲得震天响。舀到后边开水变凉水,队伍就乱套了,你拥我挤,开水溅得满地都是。打好开水回到宿舍,一把揭开大通铺上的被褥,取下馍布袋,拿出罐头瓶,拧开罐头瓶盖子,展出母亲们的爱心绝活,摆开校园“食品展览会”,馍馍、咸菜、开水泡馍在大通铺的炕沿上摆出“一字长蛇阵”“三军对垒”,大家说说笑笑,趷蹴着,把干硬的馍泡在开水里,一手拿筷,一手端碗,就着各自的咸韭菜或者油辣子,吸溜入耳,一个个吃得气壮山河,一个个喝得汗流浃背!突然,大家发现了“新大陆”,一下看到了我的“红薯杆”,红的透亮,白的鲜嫩,其间藏着的黄豆豆,还有那香油飘出来沁人心扉的味道,一下子让他们口水横流,呼呼啦啦围成一圈,你夹一筷,他吃一口,谝着课堂趣事,就着青春故事,舌尖轻抬中,半瓶已空,嘴角舞动时,瓶底已朝天,风卷残云中,使我不由得想起了《老陕咥面》这首歌: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端一碗髯面喜气洋洋,没撮辣子嘟嘟囔囔……
背馍上学时代,因为一瓶又一瓶“红薯杆”的辅佐和补给,让我在清脆利口中,豆芽式的个子不断抽条,混沌式的脑壳不断清醒,迷茫的眼神不断清澈,让我听到了三千年前《诗经》“伐檀”的声声斧响,让我读到了两千年前《楚辞》屈原的声声呐喊,让我感受到了贾谊《过秦论》的声声忠谏,让我认识到了唐诗李白的浪漫,宋词辛弃疾的雄壮,元曲关汉卿的控诉,明清四大小说的精髓……在一口口的酸辣爽口中,理解了风霜雪雨的形成,学会了多元方程式的解答,明白了娘煮米汤放的碱面就是碳酸钠,掌握了阿基米德提出的“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起地球”的杠杆原理;在一口口就馍下饭中,我走出了大山,走出了卑微,走向了诗和他乡,离星空越来越近,离故乡和娘越来越远,离“红薯杆”也越来越远。
如今。我在地上,娘在天上,当年的“红薯杆”在哪里?我想:应该在我平平仄仄的诗意铺排中,应该在我散文时评的每一个标点符号中,在我走向岁月静好的每一天灿烂烟火中。
(作者单位:运城公路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