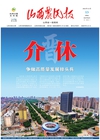火盆的记忆
小时候,家里的冬天炕上少不了火盆。尤其是爷爷和奶奶,火盆是他老两口冬日家里取暖的必需品。早年家里用的火盆是生铁铸成的,其形状类似斗笠。火盆下有四条腿做的木架,十分笨重。
节令进了“三九”,天气十分寒冷了,家里就开始用火盆取暖。在火盆生火不能放炕上,因为有些柴禾点燃后易爆火星,核桃树柴和黄芦柴点燃后就常常“噼里啪啦”地冒火星,柿树柴则流白沫沫,干柴爆出的火星落在炕上就会把被子和线毯烧出小洞。因此,火盆生火先放在屋子的地上,放上短柴或玉米棒,先用火柴点着麻秸秆将火盆的柴禾点燃,待到燃的烟雾小了,柴禾不迸火星了,就把火盆端在炕上。在火盆生火十分讲究技巧,柴横七竖八堆在一起则不易点燃,母亲说“火要虚心”和做人一样,尤其是玉米棒,如果你乱七八糟堆在火盆里,一是不好点燃,二是燃着后烟雾很大。母亲很会用玉米棒生火,她将玉米棒围成圆筒形从中引燃,既不怎么冒烟,火苗燃得也很旺。
生铁铸的火盆,工艺不精细,放屋子很不美观。那时武乡人,冬日便有人赶着毛驴车拉的砂锅和火盆来村上换柿子,我父亲就用50斤柿子换了两个火盆。这泥土烧制的火盆比生铁火盆样式美观。
用柿子换的两个火盆,父亲给了爷爷奶奶一个,我家留了一个。在既住人又做饭的门钻风、窗透气的三间土坯房内,一盆火就是一个小太阳,冬日奶奶坐在炕上的火盆旁边戴着老花镜给我爷爷补衣、补袜。我母亲坐在炕头靠近火盆给我们做鞋、缝补衣服。母亲说,没有火盆,手冷脚冻的针线活可是做不好。我过年穿的灵动秀美的猫头鞋和新衣服多数就是母亲在火盆旁和煤油灯下做的。
家里不用的生铁火盆,我爷爷则派上了用场。爷爷天冷也闲不下来,下雪天他便一头扎进那仅有一间房大小的木工屋里,做木匠活儿。爷爷生火有柴,做家具时锛砍、斧劈、刨推下来的木片、刨花,扔进火盆一点就燃,既取暖又能架上铁架熬水胶粘木板,一举两得。
那个年代,家家日子都不富裕,冬天我兄弟姐妹的身上就只穿棉袄,棉裤,袄裤里面根本没有衬衣和衬裤可穿。那时,年少好动贪玩,东跑西跳,星期天还得和小伙伴去拾柴或抬烧土、跑跳多,劳动多,出汗也就多,棉袄、棉裤有时被汗洇湿,之后热身又慢慢暖干,因而,棉袄棉裤的里面磨得十分光滑。早晨起床时穿棉袄,穿棉裤里面硬邦邦、光溜溜的,像是一块薄铁片,很冰凉。所以,每天早晨起床时,母亲生着火盆,给我们烤一烤衣服,我们趁热穿上。
母亲如忙得顾不上给我们烤衣服,我们就把衣服抱在被窝暖暖,但暖不热里面,穿衣服像是进冰窖似的。因而,三九寒天多数时候母亲都用火盆生火给我和弟妹烤衣服。
火盆还具备烤箱的功能,冬天家里有了柿子,有时母亲约莫我兄弟姐妹快放学回家,就把柿子放在火盆边,我们一回家软柿也被火盆里面的余火烤得焦黄,回去趁热吃,那味道甜中带香着实沁人心脾。
难以忘怀的是,爷爷在正月招待他的好友。他用火盆取暖就不用柴禾而是用木炭了。他先把火盆放些细柴点燃,然后放上木炭,燃旺的木炭火很温和很少爆火星,基本无烟。爷爷用锡壶倒上北方烧酒置于火盆内慢慢温热。炕上放一小方桌,奶奶炒两个小菜:豆腐和鸡蛋。他和好友围着火盆碰杯把盏,饮酒聊天,谈古道今,十分惬意。爷爷待客在当时是村上少有的景致。村上没有几家有爷爷这样待客的水平。爷爷是木匠,手艺可算一流,又因他抗战前在省城太原给阎锡山修建过督军府,故爷爷在十里八乡很有名气,他做的家具无论样式还是质量都非常过硬。他一年四季不缺营生,手头也就不缺钱。爷爷家里有了客人,嘴馋的我耐不住性子,就想进他的屋子瞧瞧,奶奶炒的那金黄的炒鸡蛋和那细嫩的豆腐块,我看得直流口水。有时候,爷爷也会叫我去吃几口,但母亲每每不让靠边。火盆里的木炭燃着红红的火苗,映着爷爷和客人红扑扑的脸,至今难忘。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火盆渐渐被火炉取代了,而近几年用火炉取暖的家户也不多了,不少家庭还装上了暖气,在农村电暖器取暖也不是新鲜事,就是空调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年轻人哪还知道有火盆取暖这一说。而我却忘不了火盆带给我的温暖。更重要的是火盆里有我快乐的童年,有我浓浓的母爱。
侯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