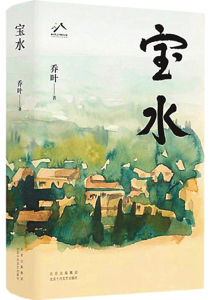在柔软中感知温暖
——读乔叶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宝水》
从《最慢的是活着》里晕染出来的柔软,在时光中延展,多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宝水》,这是乔叶关于“柔软”的又一次诠释。
在太行山麓,一座小村,树木葱茏,花草遍地,乔叶构筑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宝水村”。全书以主人公“地青萍”的第一视角进入,渐次展开乡村图景,不同角色依次登场,一幅灵动版的“富春山居图”展现在读者眼前。真实感人的情节加之对宝水风物的细致解读,让读者身临其境,仿佛置身其中,成为一名“宝水人”,不管是三梅,还是大小曹,还是其他人,都极具个性,很容易对号入座,想成为那样的人。
《宝水》以四季分章,春夏秋冬各有特点,对应全书。开篇冬—春,由落寞到萌芽,“我”因为失眠多梦,寻求一处安放焦虑的地方,便来到了宝水,这一章较为贴合主题;第二章春—夏,由萌芽到葱茏,人情的相熟到树木的繁茂,宝水村各色人等的变化,有了一定的渲染;第三章夏—秋,由葱茏到收获,美丽乡村终于发挥其价值,游客络绎不绝,人情浓郁,也算贴题;到第四章秋—冬,“镇村之宝”九奶溘然离世,由收获到落寞,宝水村的故事也画上了句号。
阅读《宝水》并未感觉在阅读一部小说,而是像在读一部舒缓的散文,或者说散文诗。每一个句子极尽柔美,淡雅,舒朗,节奏欢快,韵律鲜明,又因了章节短小,读罢一节忍不住再续一节,读罢一节忍不住再续一节,就这样跨过时光的漫流,白日尘光漂流,夜间灯光氤氲,书本捧在手里总是放不下,总想延续这种舒适,这种欲罢不能的舒服。
这种舒服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柔软”。文字精致的柔软,情感延绵的柔软,人际关系的柔软,景物描写的柔软。
“野杏花跟着漆桃花的脚,开起来也是轻薄明艳……”
“起初,红还不是秋山的主调……”
“静的空当里,就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响动……”
柔软让原本悲怆和苍凉的山村活了起来,让原本稀松平常的人情暖和了起来。这种柔软,如夜莺般歌唱。
夜莺喜好在夜间歌唱,就着皎洁的月光去聆听,宛若天籁。
这便是乔叶的高明之处。以娴静书写伟大,以舒缓衬托激荡,在看似缓流的境遇中,在平铺开的若干条线索中,不疾不徐,一步一步,缓慢而温情地牵引着读者一直追寻,一直期待,直到文字结束。
回看全书四个篇章,我们能找到很多印象深刻的点,比如方言的应用,赞扬叫“卓”,聊天叫“扯云话”,散步叫“悠”……读来妙趣横生;比如人物的刻画,“看透乡村性格”的乡建专家孟胡子,耿气爽朗的村干部大英,固守村庄规则的奶奶,天真可爱的支教大学生……读来可爱可亲。但是总觉得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像炒菜少了味精,那一撮调剂一直勾着读者的心,一直期待出现,直到全书读完都未遇见。
合上书,那缺少的味道就明显了起来——少的那一点味道就是乡村的落后和愚昧。乡村并不是只有美好,还有它“私”的部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人独特的“私”的个性,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在书中将中国的格局比作“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相同。每个网络都是以“己”作为中心,每个网络的中心也各不相同,这就是一个“差序格局”。这就出现了针对一件事情,有的人顺应,有的人抗拒,而且多数人会抗拒,毕竟变革是痛的,是艰难的,在以“己”为中心的伦常中,谁也不会去尝试改变。变革必定以少数人的牺牲开始,付出一定代价才能达到目的。这在《宝水》里是缺失的。村庄的愚昧和落后不可能一下改变,大概在作者的心目中,“宝水”是理想化的乡村,是打破“差序格局”的乡村。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乡村是复杂的,需要在“痛”的过程中,揭一层皮,剜一块肉,何其难。纵观全书,没有出现很大的冲突,没有出现激烈的矛盾,好像所有的村民都如一群绵善的羊,跟随着牧羊人的指引,到达“指定”位置。
不过话说回来,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即便是有一丝缺憾的《宝水》,也丝毫不能掩盖其天籁般的书写。语言特殊鲜明,人物塑造出彩,景物描写精美,章节划分合理,就连突然插入的叙述都没有突兀感,和谐的场景让我们又一次回到了夜莺的欢唱,在柔软中感知温暖,在柔软中接收浓情,这大概是阅读《宝水》最大的收获吧。
毕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