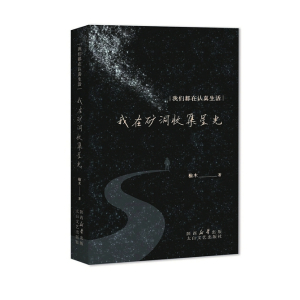唯有深入黑暗 才能看见真正的光
——读榆木诗集《我在矿洞收集星光》
诗人榆木以10年井下劳作的亲身经历,将煤块的沉重与星光的轻盈熔铸为思想深邃的诗行,并结集成册,命名为《我在矿洞收集星光》。诗人将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元素并置,揭示出他诗歌美学的核心策略,那就是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寻找诗意的可能。“矿洞”与“星光”,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符号在诗集中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辩证关系,构建出一个既向下掘进又向上仰望的诗歌空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意象的对立统一,更折射出当代人精神困境与自我救赎的探索路径。
黑暗与光明的辩证书写
“矿洞”在榆木笔下从来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地下空间,它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既是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对自然掠夺的伤痕,又是现代社会个体精神被困的隐喻,更是诗人主动选择的沉思场域。榆木在《巷道》中写道:“每向前走一寸,黑暗就多一寸,我们要挖多久,才能挖到光”。这时,他们手中的钻头既是开凿煤炭的工具,也是叩击光明的圣器。“黑暗多出两米”“西村升起的月亮”等意象,将机械化的劳作升华为对生命韧性的礼赞。
与此相对,星光这一意象在诗集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它不仅代表美好与理想,更被诗人转化为一种在黑暗中主动收集、保存的希望。矿灯在漆黑巷道划出的弧线,既是生命轨迹的隐喻,也是“被大地私藏的星光”,将梦想转化为可触碰、可保存的存在。星光在矿洞这一对立环境中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因黑暗的衬托更显珍贵,这种意象的悖论式运用构成了诗集独特的张力。
地域经验的诗性重构
作为山西本土诗人,榆木的创作深深植根于煤炭大省的地理基因。诗集中的“东翼采面”“西翼掘进”等专业术语,不仅是矿工作业的真实记录,更成为丈量生命的特殊尺度。当他用巷道标记人生重要时刻(如婚期、子女出生),实际上完成了对时间维度的重构。在井下没有钟表的世界里,煤壁的纹路、岩层的走向、矿车的辙痕,都成为记录生命轨迹的特殊“年轮”。
矿工身份在榆木诗歌中具有关键意义。诗人不是以旁观者姿态观察矿洞,而是以亲历者身份书写:“我们每天都在一块黑乎乎的煤里/练习一朵花的盛开。我们每天/都在六百米深的地下,小心翼翼地/修补自己”(《在坪上》)。这种身份认同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质朴的真实感。诗人通过“从井下走到故乡”的想象,暗含对土地与身份归属的追问,通过矿工视角将个体经验提升至普遍人类处境的高度。
抒情主体的觉醒与超越
从诗人榆木的第一本诗集《余生清白》到这部新作,他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精神嬗变。如果说《余生清白》更多是个体创伤的倾诉,那么《我在矿洞收集星光》则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跨越。诗集从个人记忆(《壬寅春》)到群体观察(《煤矿工人的一天》),情感层层递进,最终回归对生命本质的追问(《五十米巷道》),展现从个体到普世的叙事张力。从具体的井下生活,到抽象的生命哲思(《一瓶可乐的空间叙事》),再到对亲人的深情呼唤,形成了从物质到精神、从现实到超验的立体抒情空间。在《乌鸦十八章》等思辨性作品中,以乌鸦等为载体,探讨人性、命运与永恒等终极命题,使煤矿题材突破了地域限制,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他不仅重构了诗歌空间,更暗示了另一种认知可能:真正的救赎或许不在远方,而在深处。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是对诗歌精神的庄严正名。榆木的诗歌如同矿工的头灯,只能照亮有限的范围,却也因此显得真实可贵。这种在限制中寻找自由、在黑暗中收集光明的诗歌实践,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文学姿态。正如作家聂尔所言,这些诗行“带有大地的力量和沉重”,它们不是飘浮于云端的高蹈之作,而是深深扎根于矿井深处的精神图腾。
榆木用沾满煤灰的手掌收集的星光,最终汇聚成照亮人性深渊的灯塔。这或许就是《我在矿洞收集星光》给予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礼物。这部诗集的意义,恰如其中诗句所喻:“煤也需要一条通向人间的路。”他让被遮蔽的群体与情感,重新抵达光明。当我们在城市的霓虹中迷失时,不妨读一读这些来自大地深处的诗句,它们会让我们重新触摸到生命最本真的温度。
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