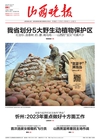父亲给我们当理发师
又到了“龙抬头”的日子,不由想起了童年时,父亲给我们当理发师的岁月。
上世纪60年代,每到“二月二”的时候,都是父亲忙碌的日子,他不仅是家里几个孩子的理发师,也是左邻右舍的义务理发员。
小的时候,我经常随父亲一同去理发店理发。那时,父亲单位每月都会发理发票,一月理一次,有理发票就够用了。到我十来岁时,从小寄养出去的两个弟弟也回到了父母身边,家里就有了四个男孩子,父亲单位发的理发票显然不够用了。我们哥几个到理发店理发不仅麻烦,而且对于每月只有52.5元工资的父亲来说,每个月的理发费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这笔支出对于全家人来说还是有点奢侈,属于可以节约的项目。
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父亲决定自己动手,于是就买了推子、剪子等理发工具,开始学着给我们理发。抽了个星期天,父亲就给我们身上围个围裙,坐在木凳上,先从我开始“下手”。爸爸虽然反复看了理发推子的说明书,学着理发师理发,但对于需要实践的理发技术还是不能很好的掌握。理发速度快了,就会夹住头发,疼得我直掉眼泪。理得慢了吧,碎头发多不说,还不出活儿,理个发时间长不说,头发还是“坑坑洼洼”的。除了头顶外,为了把头发“找平”,下边的头发都快理光了。每次理完发后,打盆热水,洗干净,就着急着出去和小伙伴们玩了,常常会被讥笑理了个“锅盖头”。刚开始,我父亲一说理发,我门兄弟几个心里就发憷,不仅不情愿,还有些抗拒。
为了调动我们兄弟几个的理发积极性,爸爸也采取了一些“物质刺激”。常常给我们许愿,理完发后可以改善生活,比如吃顿烩菜大米、肉炸酱刀削面,或者是炸油条之类的,甚至理完发之后,还会有饼干、面包、糖果之类的好吃的。在美食的诱惑下,我们也就“屈就”了。后来,爸爸在我们头上经过多次实践,技艺得到了不断提高,不仅理发速度快了,不夹头发了,发型也顺眼了,我们对父亲的理发技术也认可了。
夏天理发,我们就在宿舍院里理,不仅亮堂,也凉快。院里的小伙伴有时会围着看热闹,爸爸看到他们头发长了,就会说:“给你也理一下吧?”小伙伴们也就半推半就的,让父亲给理了发。
时间一长,父亲的理发技艺得到了邻居们的一致认可,加之他和蔼热情,“二月二”等特殊的日子,理发店人满为患时,院里的小伙伴就都来找爸爸理发,爸爸总是热情服务,来者不拒,有时上午理不完,下午接着理,一天能帮十来个人理发。
我插队以后,由于在郊区农村,每月都能回家,头发长了还是由父亲理发。参加工作以后,平时去理发店理发,但过年或“二月二”时,还会由父亲帮我理发,直到成家,不和父亲在一块住之后,才不用父亲理发了。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每回理发就会怀念父亲,就会感到特别温暖,让父亲给理发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幸福。
梁建军(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