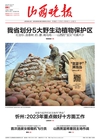潘老公卖粉浆
早年,每到初春的清晨,大同城的街巷便传出这样的吆喝声:“盛粉浆喽——原粉的。”四合院的人们听到这声喊便会跑出去打粉浆。
卖粉浆的老头身着土布衣裳,肩挑一担木桶,步履瞒跚而来。这时,许多最先跑出来的打粉浆的小孩子们就端着小盆迎上去,争着把手里的小子儿交给他。那位被大伙唤作潘老公的老人喜滋滋的,用他冻得红红的起满了茧子的手拿起木桶边挂的铁瓢,把粉浆给孩子们舀上。
粉浆,现在的年轻人可不知道这是一种啥吃食。那会儿,大同城里有不少糖坊,像南门的张糖坊,东门的施糖坊,北门和西门的晋糖坊,太平楼附近的章糖坊等,都很有些名气。这些作坊专门踩制麻糖、熬煮糖稀,一到春季又兼营制粉业。那阵子,头天把豆类品磨制成面粉,第二天拂晓加工成粉面,剩下的粗浆就是粉浆成品。
市民们买回粉浆后,一般用于熬饭,用它掺和,熬成的小米稀饭颜色呈乳白,稠糊糊的喝进嘴里有股奇香,甚是可口。
当年,糖坊出锅的有扁豆粉浆、绿豆粉浆和高梁粉浆三样,各有特点,其中数扁豆粉浆味道最好,高梁粉浆外表略呈粉色。因此,这些粉浆掺和在小米中,有时也会出现淡绿、淡粉色。潘老公经常卖的是扁豆粉浆,用它熬好的小米粥是乳白色的。
说起潘老公,此人在城内贩卖粉浆是出了名的,这位老人原是鼓楼东街薛轿房的轿夫,因轿房不会通年有活计,不能维持家用,他便利用闲时贩些小菜、粉浆,赚点钱过活。听人说,潘老公当轿夫是和他父亲学的,据说其父庚子年间曾抬过从皇城逃难来的慈禧太后。那抬轿的功夫可不简单,有“四稳”的讲究:起轿要稳,遇坡要稳,见坑要稳,落轿要稳。有这样的腿功,潘老公后来挑担沿街串巷卖粉浆是不成问题的,木桶里的粉浆死沉死沉的,压不稳步子的人挑起来左右晃动,会翻桶。
有人也许会问:“这粉浆为啥受欢迎?”因为旧时穷人多,粥是百姓天天要喝一顿的,熬纯小米粥,谁舍得?粉浆便宜,掺和上,可以省下小米,自然十分抢手。
在老大同的记忆中,潘老公那时已六十多岁了,但仍然每天早早地去糖坊接上一担粉浆出来贩卖。后来,他叫卖的气力明显不足,担起担子也开始颤颤悠悠了,看着不免令人心酸。
而今,粉浆已经很少出现在人们的饭食中了。
刘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