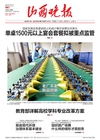草蔬岁月
“嫩焯黄花菜,酸韲白鼓丁,浮蔷马齿苋,江荠雁肠英。燕子不来香且嫩,芽儿拳小脆还青。烂煮马蓝头,白漉狗脚迹。猫耳朵,野落荜,灰条熟烂能中吃;剪刀股,牛塘利,倒灌窝螺扫帚荠。碎米荠,莴菜荠,几品青香又滑腻。油炒乌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茭儿菜,四般近水实清华。看麦娘,娇且佳;破破纳,不穿他;苦麻台下藩蓠架。雀儿绵单,猢狲脚迹;油灼灼煎来只好吃。斜蒿青蒿抱娘蒿;灯娥儿飞上板荞荞。羊耳秃,枸杞头,加上乌蓝不用油。”这一大篇幅的内容讲的是一桌子野菜宴,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近四十种名称的植物绝大多数人并不熟悉,也不认识,年长之人也不过偶识几种。这是《西游记》八十六回中,被救樵夫和他的母亲为感激唐僧师徒四人而置备的一桌子“菜”,至少有三十七八种。想来,樵夫母子久居深山之中,想要一时三刻置办出这么多种类的“蔬菜”,是断然没有菜市场可以逛的,假设就是到当今的菜市场去采购一番,也至多不过十几种菜蔬而已,无法与山野品种丰富的野生植物相比较。
今人读来,这些摆上桌子的“菜”,不过都是野草罢了,即便是端上餐桌,大抵也只能叫“野菜”,不能与日常食用的蔬菜相提并论。其实,那些生活于山野间的草发展到餐桌上的菜,中间隔着的就是岁月。
东汉时许慎《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菜,草之可食者”。“药,治病草也”。也就是说,菜、药,本就是草,只是因了功效差别而被赋予了新的名称。
秦汉之前的本草类书籍中是没有菜这个类别的,而是以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来记录草本植物,直到魏晋南北朝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才首次将“菜”从“草”中分离了出来。陶弘景则根据实际用途分为玉石、草木、虫善、果、菜、米食、有名无用七类。将韭、葱、芥、苋、鸡肠草、荠菜等三十余种植物归入菜类,从而使蔬菜成为与草木药品平行的一个独立大类。有世界第一农书之称的《齐民要术》也采用粮食、油料、纤维、染料作物、蔬菜、果树、桑树、禽畜、鱼类的分类方法。自此以后,这种分类方法为历代所沿用,蔬菜正式脱离了“草”的范畴。农耕时代,粮食产量远低于现代产量,且从事耕种的人口数量也很少,加之生产力低下,保证粮食产量才是根本,蔬菜的需求几乎都是通过采集野菜来满足日常所需的。唐代时,还曾有一个专门为采摘野菜而设的民俗节日——“挑菜节”。据史料以及唐诗记载,当时,京都长安的人们,为了活跃生活,每到二月二便三五成群地到郊外踏青,有些妇女提篮执铲去挖鲜嫩的荠菜佐食,把这一天定为“挑菜节”。唐代时农历二月的气候与现在不同,而且长安以及晋南的温度要暖和很多,地里生长的野菜正在返青发绿,这是一年里野菜最嫩最具营养的时候,一些野菜正当时。
挑菜节的风气起于长安,随后各地也跟着流行开来。这个节日在我省的河东地区(今运城一带)甚为流行,并发展成为当地的一项民俗。每年农历二月,麦苗返青、野草萌发,几乎家家户户的妇女儿童都要臂挽竹篮,手执铁铲,到麦田、山野中去挖野菜。“二月小蒜香死老汉”是河东地区一句俗谚,至今二月时节,一些山区的村民们还会去挖野菜,特别是这种长着黄豆般大小蒜头的野菜,包饺子、炒鸡蛋,甚至还腌制好储存起来慢慢吃。而且在河东一带素有春季遛百病的说法:“春季田间游,百病不露头”“阳气吸在身,百病不缠身”,这种挖野菜的民俗,正好是踏青、遛百病的活动。而且挖野菜的民俗大多在麦田中进行,可以借此除去田间的杂草,保证麦苗的正常生长。
自元入明清,挑菜节突然便消失了。明前期的一百年间,黄河流域水灾凶猛,山陕两地旱灾高发,旱灾过后又是蝗灾,“黄尘四塞”“雨黄霾”,而且沙尘暴也从明代开始肆虐。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变得恶劣。野菜从此几乎与饥荒画上了等号,挖野菜成为一种苦难生活的表示,不再是生活的情趣。
又是百年时光,现代农业的发展,让粮食种植和蔬菜种植大面积发展,餐桌终于实现了蔬菜自由,野菜与饥荒彻底决裂。春日里餐桌上的野菜,成了稀罕,成了调剂,成了一种回味。踏青时若能再挖几丛野菜,再度成为了生活中的一点情趣。
山西晚报记者 李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