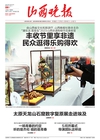回忆旧时“龙抬头”
夜幕中散步,路过一家理发店,忽的想起二月二前遇到的一件事。那天,街边理发店发出了争吵声,循着涌动的人流看去,原来是顾客与老板为加价的事而争吵。顾客持会员卡,老板非让再加价五块钱,理由是快到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了,理发者太多。其实商家这样在节日加价的情况司空见惯,对于洗车店或理发店里重大节日不能用卡或卡外加价的情况,久居城市里的人谁没有遇到过几次?最终在商家的坚持下,钱还是照付,毕竟彼时头发已经理到了一半。
在儿时的记忆里,二月二除了理发,还是有不少礼数和讲究的。孩子们还在被窝里的时候,母亲便早早起来,将干透了的“枣山”摆一块放到枕头边。按照习俗,未成年的孩子这天睁眼后第一件事就是“咬蝇子”。现在想起来,那个坚硬的程度实在是不好啃,但一来毕竟属于白面馍,是难得一见的稀罕物,二来据说只要二月二早晨咬过“蝇子”,一年里就不会受苍蝇蚊子的叮咬,孩子们还是会欣喜地去啃,但究竟起多大作用,想必没有人去深究。事实上生活在山里的孩子,一年中是免不了受几次蝇虫之苦的,但一些风俗习惯就是在这种将信将疑、年复一年的美好愿景中慢慢传承下来的。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蒸“枣山”,将发好的白面捏成三五个如意状的小卷卷,每个小卷卷都夹上红枣,再捏头部和腿部,头部像一个官帽子,中间也夹着红枣,两条腿的胯部也都夹有红枣,然后在案板上将捏好的部分按头腹腿的顺序黏在一起,用菜刀将其送到锅里蒸,十多分钟出锅后立起来,活脱脱像一座用白面和红枣堆砌而成的小山。大年初一早上,“枣山”要在灶台后面、屋门上边各放一个。此后白天放、晚上拿,生怕被猫或老鼠叼走,直到过完正月十五,干透了的“枣山”才被收了起来。
二月二的早饭须吃饺子,叫“捏龙口”。听老人们讲,龙抬头,把龙口捏住,为的是不让龙的口空着,这是对龙的崇敬;早春二月,见龙在田,让吃饱喝足后的龙腾飞九天,普降甘霖,“捏龙口”又有对龙的畏惧,让其吃饱后就不会吞噬其它动物,图的是六畜兴旺、平平安安。馅是胡萝卜拌上咸盐花椒红皮葱,如果能再放点儿白豆腐,那就是非常好的馅的了。在白面奇缺的年代,二月二的饺子多用高粱面,由于黏性差,通常要放点榆皮面,这样面才能捏到一块。榆皮面就是将榆树的皮或榆树根部的皮趁湿剥下,晒干后用斧头砸成小块,然后用碾子或石磨磨成面,是吃高粱面的必须之物。
为了全家在午后能吃上一顿二月二的煮豆子,女人们在早两天就忙碌着开始准备食材,自家凑不齐的要提前与邻居家调换。那时没有高压锅一类的灶具,这些食材需先浸泡两天才可以用炭火煮透。煮豆子的食材通常有红豆、豇豆、豌豆、扁豆、小麦、玉米等五六种,寓意五谷丰登。最具特色的是上年收获的小蔓菁,指头般大小,秋天里洗干净后用针线穿起来挂在门外的墙壁上,经过一个冬天的风吹后略显干瘪,也得与豆子们一样提前泡上。别小看这个小蔓菁,它可是二月二里一碗煮豆子的魂。有了它,煮熟的豆子就没有了生硬气和寡淡味,才能吃出那种淡雅柔和间透出的清香味。
二月二前前后后最忙碌的当选村里的剃头理发师傅。老辈人用的是剃头刀,就像影视剧中演得那种,背部厚厚的,刀刃薄薄的,带一个短把,可以拉得开合得住。剃头时将头发用碱水洗干净,然后用刀慢慢地刮。如果剃光头倒也省事,从上至下几个来回就差不多了,难的是剃偏分头、小平头一类,没有个把小时是完成不的。而村里剃头刀就两三把,会使用的也就三两人,从早到晚都完不成,后来干脆从初一开始连剃三天。随着推剪走入乡村,再后来削发器的兴起,理发的效率提高了几倍,理出的发型也漂亮了许多,年轻人都不再用剃头刀,但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喜欢它,说刮得舒服。但不管是使用什么工具,村里的剃头理发师傅都是义务的,即使大家的日子是那样的清苦,但剃个头理个发全然没有任何费用,当然也就没有城市里街头边为了涨不涨价的争吵。有时闭眼睛想想儿时人们排着队,一个接着一个在欢声笑语中去剃头理发“龙抬头”的情景,不禁暗暗摇头发笑,那是一幅多么温馨和谐、却又不可能再回得去的田园美景啊!
□薛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