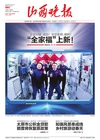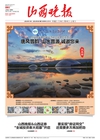葱香四季
秋叶纷飞,冬季将至。
循着四时生活的人们,开始为冬天的到来做着准备。“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笔下的塞北高原在这个时候已经飞雪连天。尽管今秋的气温着实要温暖很多,但是依着几千年来的生活习惯,这时已经到了秋收冬藏的时节。在大地封冻之前/飞雪未到之时,必要的储备还是要进行的。超市挂出了“冬储菜是入冬仪式感”的条幅,囤菜是北方人对冬天最大的尊重。除了必不可少的白菜、土豆、萝卜,还有一样蔬菜是家家都会囤几捆的,那就是大葱。家家买几捆回来,都解散了摆在通风处,跟其它冬储菜比起来,十分招摇,也就成了冬季囤菜开始的标志。只要院子里看到有人摆出大葱晾晒,紧跟着用不了几日,大葱就随处可见了,街头专门兜售大葱的农用车也会及时地停小区门口,方便人们采购。
北方囤大葱的风景在很多南方人眼里是稀奇的,毕竟南方的小香葱,纤细柔弱,一年四季都水灵灵地摆在菜摊上,不像北方的大葱粗壮高挺,甚至比一般人的身高都要冒出那么一截,若非亲见,着实是无法想象的。而大葱的得名,也正是因为它长得高大。不过,踏入中国土地的三千多年中,大葱的面貌也是有所变化的。
早在公元前681年,《管子》一书中记载:“齐桓公五年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子天下。”山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族名,原是盘踞在中国北方燕山山地的一支游牧部族。近3000年前,葱在北方的旷野上恣意生长,且这种葱可以越冬。至今,北方的冬储葱与土豆、胡萝卜、红薯这种冬储菜不同,依然保留着不怕冻的特性。
大葱在北方的旷野里成片地蔓延着,如今的帕米尔高原,曾是古代的葱岭,它的得名便是因为漫山遍野长满了葱。“葱岭者,据南赡部州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地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公元629年,大唐的玄奘法师从长安出发,当他途径葱岭时,被漫山遍野青翠的野葱震撼到了。而今的大葱,三千多年前就已经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以及商人的脚步,从葱岭逐渐遍布到中国北方的土地上。
汉朝时,种大葱已经是一项农业种植任务。汉朝《汉书·龚遂传》载:“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五十本葱。”葱在古代时多栽种于半寒冷地区,这也符合葱的生活习性。汉代,崔寔撰写的《四民月令》中记载:“二月别小葱,六月别大葱,七月可种大小葱。夏葱曰小,冬葱曰大。”可见,大葱已经成为了汉代主要的作物之一。
汉代时,人们不仅认识到了葱的调味作用和食用价值,更主要的是它的药用价值也已经被医家所认识。张仲景《金匮要略》中就有用葱的药方:“旋覆花汤方,旋覆花三两、葱十四茎、新绛少许。”并且还在“果实菜谷禁忌并治”中对葱的食用禁忌做了强调。
到了元代,葱已经妥妥的成为了农业种植中的蔬菜品种。元代王祯编撰的《农书》中记载:葱,说文,曰:“荤菜也”;其色葱故名。凡四种:山葱、胡葱、汉葱、冻葱;尔雅,曰:“茖”,即山葱,宜入药;胡葱亦然;食惟用汉葱,冻葱耳。汉葱叶大而香薄,冬即叶枯,宜供齑食;冻葱叶细而益香,又宜过冬,比汉(葱)为胜,或名大官葱。陆放翁,诗:“芼羹僣用大官葱”。王祯除了介绍了葱在这一时期的几个品种,还详细介绍了它的种植方法,并且对葱做了一番评价:“葱之为物,中通外直,本茂而叶香,虽八珍之奇,五味之异,非此莫能达,其美是犹商梅之调鼎,吴橙之芼鲜也,其可以他菜而例视之哉!”王祯认为各种食材想要达到美味,是离不开大葱的。
山西在历史上曾是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地方,山戎在唐虞之前便生活在晋北桑乾河流域,过着渔猎和游牧的生活。早在三千多年前,葱已经是这片土地的特产了。
时光越千年,大葱在山西的土地上依然风味独特。太原市小店区的鸡腿葱曾经是做山西过油肉的绝佳配菜,葱白紧实,久经翻炒而不散;晋城市巴公镇的大葱曾是山西省早期四大名优土特产之一,巴公烧大葱还是当地的特色菜品;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万泉乡的万泉大葱,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山西农家即便不是大面积种植销售大葱,也都会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上几垄大葱,毕竟这滋味是刻在基因中的。
山西晚报记者 李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