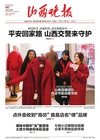年味儿故乡浓
回乡过年,当车从高速下来,拐个弯,就抵达了故乡。
乡间,较之城里,气温略低,但空气清新。远山如黛,小溪似带。青白色的水泥路,如一根根筋脉,连着大大小小的村庄。长满狗尾巴草的田埂,纵横交错,镶嵌着碧绿的油菜、青青的小麦,俨如一轴清丽的田园水彩画。杂树丛里,喜鹊们蹦蹦跳跳,发出喳喳的欢啼,黑缎子般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幽幽的蓝光。
已进入除夕“倒计时”。沿途不时有小车呼啸驶过,驶向各自的家园。车窗里,映着一张张喜悦的、似曾相识的面孔。
沿途的村庄,宛如一座座戏台。回乡的人们与亲人们一起,依照传统习俗,正在为春节这一场大戏忙碌着。笼罩村庄的,是喜庆的节日氛围。屋檐下,挥舞长扫帚的,是在掸尘;打谷场,挥毫泼墨的,是在写春联;村广场上,载歌载舞、敲锣打鼓,是在为节日演出彩排;屋顶上,炊烟袅袅、美味飘香,是在忙着准备年夜饭……
春节,热闹的是人。平日清寂的村庄,因为大家的归来,变得沸腾了起来!
家,依旧是生我养我的老家。从姐姐、我、弟弟、妹妹长大各奔东西后,母亲长年一个人留守家里。渐渐地,我们有了自己的新家,有了孩子。如今,拖家带口归来,已是十好几口人。
由于一年才相聚一次,我们格外珍惜。考虑到这么一大家子,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从各地带回了“网红”美食。然而,令我们想不到的是,母亲却坚持遵照习俗,一样不少地准备好了传统的主打菜——鱼糕、肉丸、风鸡、藕夹、蹄膀、腊肠、酱板鸭、卤牛肉、排骨藕汤、羊肉火锅等等。在熊熊灶火的映照下,它们弥漫着浓浓的香味,将我们这一群游子沉睡已久的味蕾唤醒。
遵照故乡习俗,过年不能忘了先辈。落日余晖里,乡亲们在吃团圆饭之前,虔诚地完成了祭祀。当然,我们也不例外。
当贴完对联、年画、门神,在屋檐、院门、树枝挂上红通通的灯笼,恍惚间,一年的最后一个夜晚降临。开始吃团圆饭了!“噼噼啪啪——”一刹那,十里八乡,电光火石,爆竹声声,此起彼伏。夜晚的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与此同时,“轰隆——”,仿佛春雷滚滚,深蓝色的空中,一朵朵烟花璀璨绽放,声音在夜空里回荡,传得很远、很远。一时间,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大家共叙团圆之情,共享天伦之乐。
辞旧岁,迎新年,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是多么的难得!凝望着母亲在亲人们的祝福下两眼泛潮,我忽然领悟到过年的意义:它,其实是在一年一年的轮回中,让血浓于水的亲情凝聚,引领我们回到生命的起点,寻找活着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真谛。
同时,我也凝望着我十四岁的儿子,在城里长大的他,一年一年回到乡间过年,在他生命的年轮里一定会留下“年”的记忆,一代一代将“年”的基因延续。
“十、九、八、七……四、三、二、一!”时针,分秒不差地跨向新年。一刹那,烟花、爆竹再次点亮、响彻了十里八乡。旧年,像我当初毅然决然离开故乡一样,不肯停留;新年,也像我如今不管不顾归来一样,兀自呈现。
按照传统,该守岁了。母亲在床下、角落里点燃了一盏盏灯,一家人坐在亮堂堂、明晃晃的烛光灯影里,心怀虔诚。年长者守岁,是为辞旧迎新惜福;年轻人守岁,是为长辈长寿祈福。今夜注定无眠,夜阑人静里,只听见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走个不停,让人恍惚间,仿佛回到了亘古。
天渐渐亮了。晨曦,仿佛潮汐一样涌来;除夕,宛如梦一样远去。淡青色的薄雾里袅袅,潮润的空气里,仍残留着昨夜烟花的味道。乡间的土地上,随处可见桃花瓣、梅花蕊般的爆竹碎屑。大年初一,到处是“新年好”“给您拜年啦”“恭祝发财”的祝福语,亲情、乡情、友情凝聚在一起,像三股导火索绞在一起,再一次点燃了大家的激情,让人的眼睛热热的,心儿烫烫的。
那一刻,我再一次领悟到了过年的意义:生命,就是在与时光的一次次告别中,让我们感动、凝聚、成长,带着寄托、牵挂、憧憬,从从容容,步向春天,走向未来……
□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