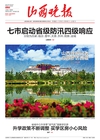难忘月下纺线线
不知多少年了,在月光洒满院落的时候,一首童谣,便在我耳边回荡:“月光下纺棉花,心里思念我娘家,娘问纺线做啥呀,织成布儿暖全家。”
入夏之后,一轮圆月从东边升起,一辆辆纺线车便从各家各户搬出来,摆放在村里的开阔地,比如打麦场,这些纺车就组成了一道别样的乡村风景。说笑声、纺线车交织在一起,是夏夜的乡村大合唱。这些已经逝去的时光,成了我心中的乡愁。
月光皎洁。妇女们坐在纺线车前,左手转动纺车的手柄,纺线车嗡嗡转动起来,带动起右边的铁锭,妇女们将搓成长条的棉絮与铁锭连接起来,随着铁锭的转动,像蚕吐丝一样,棉絮拉成一条均匀的长线,然后轻轻放入转动的铁锭中。这一切都是在熟稔的动作中飞快进行,十分自然、和谐。不到几分钟,一个棉穗就形成了,取下来之后,再开始纺另一个棉穗。在纺线的群体中,有不少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她们小学毕业父母就不让上学了,在父母眼里,她们迟早要出嫁,学会做针线活,才是真本事。母亲一板一眼手把手教,少女们认真体会,开始总是不那么协调,左手转轮子,右手就不会动了。每每看到这一情景,我心里也一阵着急。那时,我蹭在母亲身边,想学纺线,母亲就推我一把:“没出息,男孩子学女人的活儿,像什么!”
月下纺线线,不仅图个纳凉,还是一场夏日大型唠嗑大会。那时文化生活少,姐妹们就利用这一段时光在一起说说笑笑,晒晒才艺,比如唱些当时流行的小曲。当年有一段《夫妻斗嘴》的唱段,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说你呦邋遢呦,真邋一个遢呦,你头上的金丝呦乱如麻呀,咿而呦;说你呦邋遢呦真邋一个遢呦,你给妹妹买梳子,妹妹会梳呀,咿而呦。还有一段小曲流传更为广泛: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山西,离这还有三百里;痛心事莫提起,都是有家不能回,为国家当兵去,太行山上打游击。除了唱小曲,大家还会猜谜语、讲故事。有些故事,能让人笑得眼泪都流出来。
一般在大众场合,大家都不说他人家长里短。不过,有时也有婆婆数落媳妇,媳妇抱怨婆婆的,诉说委屈的也免不了。这时候大伙只是长着耳朵听,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就出去了,尽量不插话。一次,有一户人家的婆媳两人的纺车在一起,婆婆当着媳妇面说:你打小没了妈,不会织布,你的棉花我给你纺,布给你织,织好给你浆,给你做。你可好,把我的好处都忘了?再说你有了娃,我给你看娃,你能忘了?媳妇也守规矩、懂孝道,一句也不还嘴。我们乡间有一句这样的话:“有理是理,没理事大”。大人数落你,做小辈的是不能回嘴的。孝道文化,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
静谧的夜晚,不见明亮的电灯,没有精彩纷呈的电视,只有嗡嗡的纺线声。娃娃们在这里得到启蒙,做人的道理在这里得到教益,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传承……
梁冬(新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