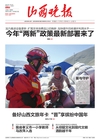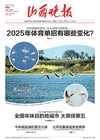行走大安
在群山环抱的福建,官台山大抵只能算一座普通的山。但在600多年前的明代,还属建宁府管辖的官台山就已经声名鹊起,大宝坑银场产银量处闽浙两省数百个银场之首,与周宁宝丰银场、景宁渤海坑银场、天台大岭口银场并称闽浙四大银场。
盛产银子的官台山因争夺财富常成为兵戎相见之地,明景泰六年(1455年),为加强监管、阻止民间盗采,取安宁之义,明政府划出政和及福安的部分区域,设立寿宁县。
因此,当地人称官台山为母亲山。大安,就在官台山下,大吉平安的寓意与寿宁同出一辙。
大熟
在晚秋的一个晌午,我们寻见大熟,大熟是大安乡一个村庄的名字。
几棵不知名的老树就在村边独自长着,我没寻见枯藤、昏鸦,但沿着老树尽眼望去,隐约可见稻浪、可闻荷香,在阡陌间,绿油油的蔬菜瓜果穿插其中。
惬意的田园风光,与孩童时的乡村景象似曾相识但却不同过往。赤脚田间捡拾田螺、爬上草垛看繁星点点,抑或是偷挖邻居家的土豆、采摘还未长够个的黄瓜。没心没肺的童年常常忽略儿时的困苦,偷挖来的地瓜、土豆,烤起来味道总觉得格外香甜。与被邻居发现相比,更担心被父母发现后的责打,友善的邻里发现了,大不了说上几句。
眼前的大熟,一位老伯正在稻田里不紧不慢地收割稻谷,乡土作家禾源与他打趣:自己年轻时也从事过农活,速度可比他快多了,挑的也多。老伯不言,笑脸依然。
纵然田园依旧,但时光早已改变,披星戴月的劳作为的是生存,不紧不慢过的才是生活。
随手拔起一根稻秆,一剥一掐,禾源便制作了一只稻笛。放在嘴里一吹,清脆的呜呜声便飘散在田野中。草垛、稻笛、清风、绿野,孩童时的野趣不知不觉中一幕幕涌出眼前。
这是几代人的童年往事,他们善于就地取材,在贫乏的生活中寻找无拘无束的乐趣。
官台山
福建多山,矿产富饶。史料记载,宋朝时,福建就已是全国主要的银矿产地,寿宁官台山大宝坑银场在当时就已经盛名在外。
除了上百个古银硐,官台山至今仍保留着冶炼、运矿道、粗制石磨以及太监府、巡检司、官司楼、官事街等大量遗存遗迹。
古人的探银炼银之法,宋代赵彦卫在《云麓漫钞》有记载:“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数十丈,烛光自照。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然后以水淘,黄者即石,弃去;黑者乃银,用面糊团入铅,锻为大片,即入官库。候两三日,再煎成碎银,每五十三两为一包。”
有宝藏的地方自然都少不了纷争。物欲横流、刀光剑影同样在官台山上演,“大宝坑”“黑风洞”“太监府”“操武地”“跑马坪”“下马碑”,从众多遗迹中,你似乎都可以看到官台山的风云变幻。
盛产银子的官台山并没有给当地的百姓带来富庶。置县400多年后,这里的百姓揭竿而起,官台山下,诞生了闽东第一支群众武装。1932年,中共寿宁特支在大安创建红带会,1933年,全县上万名红带会员相继举行武装暴动,攻打南阳、坑底等地驻敌,为耕者有其田而抗争。
官台山是一座有故事的母亲山。2020年12月,已不再产出银子的官台山古银硐群被列为国家地质公园。修葺一新的景区道路,时常车流穿梭。
一座官台山,流传着寿宁500多年的斗转星移。
亭溪
寿宁是一片神奇的土地。2013年,福建省地质勘测局在寿宁检测土壤,发现这里28%的土壤都富含人体必需的硒、锌元素。这种微量元素,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功能,被国内外学术界尊称为“长寿元素”“抗癌之王”。
中国传统村落亭溪就是个硒锌养生村:山水环绕、青瓦土墙,至今依然完好地保存着传承几个世纪的闽东民居特色,在一座座民居间蜿蜒的石板路、垂挂在土墙边的瓜果,无不昭示着这个村庄的古香古色。
我们留恋乡村,不仅仅是青瓦、石板、田园、绿野,淳朴、友善、信任、互帮互助的邻里不正是一直留存心底的美好么。
亭溪花卉种植合作社经理叶生对我们说,在他的种植园,很多年纪稍大的员工不喜欢每月领报酬,“到年底一次性领取最好,要不然会随手花了”。信任邻里,他们丝毫没有雇主会拖欠报酬的担心。合作社还发展了三叶青、猕猴桃、硒锌葡萄等特色水果500多亩,开发硒锌农产品20多种,上百名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增收。
种植园里有个百菊园,叶生选种了金丝皇菊、百日菊等菊花,花开时节,亭溪就成了游人如织的花田。
银山是大安的过往,花田是大安的今生。不同空间的两种景致,在时光里镌刻着大安的乡村变迁史。
□吴道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