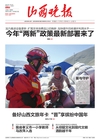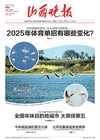堂兄
周日约了堂兄小坐。好长时间未见,他的背略显佝偻,脸颊更加消瘦,一双手指也皲裂多处,并拢双腿规规矩矩地坐着。倒是一对睫毛长长的,显得眼眸比别人机灵几分。堂兄的口才依然很好,好多年前的事情记忆犹新,娓娓道来,很快拘谨便烟消云散。临走,妻子整理了一些衣物、零食及一双崭新的运动鞋给他,装了满满四个购物袋。他双手拎起袋子,眼角似有微光:“兄弟待我比亲兄弟还亲咧!”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妻子叹了一口气:“真可怜!”
堂兄自小家境贫寒,父亲多病,母亲残疾,兄妹又多,15岁才小学毕业,上初中要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因买不起自行车便辍学参加劳动,做过三十几年的泥瓦活,拉过预制板材,现在在一家饭店当刷碗工。无论干什么都干不好或干不长,因为他骨子里始终埋着当艺术家的理想,而不是一个“受苦人”。
辍学后,他把用过的书本写字本积攒起来,练习毛笔字。到别人家串门,发现旧的书报也会当宝贝拿回家,日夜苦练。还利用打零工攒下的钱,报名参加了县文化馆组织的基层美术培训班,结识了一批文化圈的朋友。几十年坚持书画创作,乐此不疲。周围人瞧不起他,嫌他懒散不务正业,而他也不屑与周围人打交道。抱着“穷且不坠青云之志”全身心投入写生,临摹、交游、求教,技艺日见长进。家里的墙壁上挂满了他的写意画、山水画、花鸟画,栩栩如生,意境空旷。他还自制彩墨,研习油画。前不久他微信发过来一幅肖像油画作品,主角是他九十岁的姑姑,面目慈祥,棱角分明,跟真人无二致。早年,他还书写春联,拿到集市上售卖,很受欢迎。我建议他专门给过寿辰的老人画像,应当会有市场,也好创收一些,他点头应允。
小时候堂兄与我毗邻,和我一样爱听评书。一放学,他便寻到我家,找个没人干扰的角落,把耳朵凑到小小收音机旁,凝心聚神,不舍落下一句一段。那时,刘兰芳的《岳飞传》、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单田芳的《隋唐演义》等,都是我俩追捧的节目,而他好像更有悟性,听一遍便记住了,过后表演也像模像样。周围人劳作之余,想要开心时便起哄让他现场来一段。他呢?像注入鸡血似的,刚才还懒洋洋地挑不起一包泥浆,马上就能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抻一抻裤角的泥巴,往空地中间一站,手一摆,眉头上扬,评书段子脱口而出。随着他活灵活现的表演,周围干活的人都停下手来,慢慢聚拢过来,听得如醉如痴!从此,他名声大作,一有闲空,大家便鼓动他来一段评书或相声,给枯燥的工地生活注入欢快的气氛。只是不分时间的表演,总免不了让包工头懊恼、催促。
当同龄人相继盖房子娶媳妇的时候,他却把挣下的俩枣仨瓜,都用来买笔墨纸砚,收藏书报刊物,摆弄古董杂耍等,天天沉浸在自我世界,不问旁事。幸亏与兄弟分家时,分得两间瓦房,有个容身之所,但却再也凑不齐娶媳妇的彩礼钱,错过最好年龄,至今孑然一身,转年就是花甲之年了。
他兄妹五人,他与大哥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老大在村里摆了麻将桌,收点有限的租金,勉强过日。我劝他与大哥搭伙过日子,他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老大啥也不懂,我俩不是一路人,各自安好便是。”他现在早晨七点半去饭店,把前一晚上的锅盆碗筷洗涮干净;午饭后,再清理一次,一天工作两三个小时。饭店提供两餐,每月两千元的酬薪。下午三点后便自由支配了。他总结自己的生活是:“迟些早些没关系,想写想画没人管;外出访朋又拜亲,多和良友来座谈;人生苦短转眼逝,学习高人须自强!”前几天他过生日,还请了几位票友在家里聚餐唱和。他有点喝高了,直至晚上十二点还兴奋不止,给我发来他的一幅书法作品,苍劲有力的四个字:“情深意切”。他书法绘画水平不错,写作水平也不断精进。平时在微信群,经常分享一些自己写的短文章,有的还颇为生动。
堂兄外表文文弱弱,心地极其善良。与人交往,从不高嗓门大喉咙,更不沾小便宜,而且还常常接济不如他的人。几个光棍聚餐,常常是他当东家。发小乔迁之喜,他裱了自己的字画赠予对方,以示祝贺。那年南方发大水,他还捐了一百元钱。一位朋友整理他口述伯父参加革命的事迹登报后,他非要塞给那位朋友二百元,以示感谢。与他要好的一位文友英年早逝,他时时牵肠挂肚,主动提供素材,央另一位文友撰文悼念。他极爱面子,固守着自己的做人底线。
我有时想,命运真捉弄人!如果堂兄生于富足家庭,他只顾专心学艺,或许早已功成名就,又如果他能逆境奋发,或许也会家兴业兴。但生活没有那么多如果,我只能衷心祝福他,好人有好报!
□雷国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