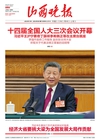过年回娘家是心灵的慰藉
四十岁的我对“过年”这件事没有太多期待,唯独期盼的就是用春节假期回娘家。
娘家,始终是我心里最暖的家和最坚实的依靠。
我的祖籍在东北,生在矿区,从小在矿区长大,所以家里延续着东北过年的老传统。对于已出嫁的我来说,东北人家的过年,那才叫有“年味”。
记忆中的年,总是从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开始。雪花在空中翩翩起舞,给矿区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我们一群小孩子在雪地里嬉笑玩耍,奶奶家窗前大杨树下的那块空地,是我们的天地,堆雪人、打雪仗,通红的脸蛋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大人们则在屋里忙碌着,为过年做着各种准备。奶奶会早早地将家里的被褥拆洗一新,让阳光的味道充盈在每一个角落。母亲会搬来梯子,仔细地擦拭着门窗上的灰尘。父亲会抱来一大捆木头,坐个小板凳,在一旁劈柴,不一会儿,一捆捆长短粗细一样的柴火,便整齐摆放在楼道旁。而我和哥哥,总是跟在他们身后,帮忙递这递那,虽然有时会添些小乱,但那份参与的喜悦却是无法言喻的。
一过腊月廿三,年的脚步就近了。记得那时,奶奶家就成了我们全家的聚集地。我家四口、二叔家四口、三叔家三口、老叔家三口,加上奶奶爷爷共十六口人一起过年,那份快乐至今无法超越。
腊月廿三是柳湾的赶集日。集市上人头攒动,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摊位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五颜六色的糖果、新鲜的水果、精美的春联,让人目不暇接。柳湾矿的“闹市区”就是那条贯穿南北的街道,一头是柳湾的标志性建筑——游艺楼,另一头通向狼虎沟教师楼前。我每天跟着母亲来来往往穿梭数次,还总被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吸引,母亲则会细心地挑选着过年要用的食材和礼品,大包小包买个不停。那时的条件虽不富裕,但是过年绝不含糊。
东北人家的过年一定是大操大办的,爷爷每年都会早早买回大半扇猪肉和数个猪蹄,接下来的几天里,烧猪头、剃猪毛、分解、蒸煮,这大半扇猪肉会被做成蒸肉、煮肉、灌肠、血肠、压花肉……在奶奶的带领下,叔叔婶婶们齐上阵,两口大铁锅一刻也闲不住,做好的肉摆满在奶奶家的箱盖上和窗台上,满满当当的。
我们家过年有东北人家的特色,也有山西的面食——油花花。做油花花的面是很讲究的,软硬度、油盐比例都至关重要。做油花花的主力是我妈,只见一大盆面在老妈手里来回翻滚,揉、搓、擀、切,得心应手。一旁的孩子们睁大眼睛看得发呆,急着上手参与其中。这边孩子们各种捏,那边大人们下锅炸,热火朝天,好不热闹。一盆盆金黄冒泡的油花花出锅,香脆酥软、香留齿间,至今难忘。蒸枣馍也是我们小孩子的最爱,发挥想象搞创作,捏成鱼的、兔的、小狗的、小花的、四不像的,各种形状的枣馍装点着不一样的新年。
大年三十一早,我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醒来,换上新衣服,穿上新鞋子,欢欢喜喜地跟着哥哥贴春联。哥哥踩着凳子,小心翼翼地将春联对齐贴好,我在下面帮忙递胶水、看位置。那一副副寓意美好的春联,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鲜艳。贴完春联,母亲和奶奶已经在厨房里忙碌起来,厨房里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气,炸丸子、炖排骨,每一道菜都饱含着家的味道。我忍不住偷偷地尝上一口,那满足的滋味至今仍留在心间。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享受着丰盛的年夜饭。大人们一桌,小孩们在炕上还有一桌,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每一道菜都有着独特的寓意。红烧鱼象征着年年有余,饺子寓意着团圆吉祥,再有幸吃出个“钢镚儿”,虽硌着牙,但却甜在心。大家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分享着一年来的点点滴滴,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房间。
凌晨12点的酸菜饺子是出嫁后的我至今忘不了的。妈妈说,“这才叫年初一的饺子”。零点的钟声一响,饺子下锅,吃着年初一的饺子,给长辈们一一磕头拜年,手捧着一个个“鼓鼓”的红包,心里比蜜都甜。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当初那群“添乱”的娃儿们如今也都为人父母了,奶奶家的老楼早已拆迁。时光不同往日,“年”也大不如前。或许时代不同,年也不同;或许往日的“趣”只适合那时的我们。
每每过年,心中都有无尽感慨,感慨岁月流逝,感慨已到中年,唯独幸运家中父母虽已古稀之年,但依然精神矍铄,会给我们准备各种美味,依然可同我们谈笑风生。过年的那份期待和喜悦似乎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浓烈,但每当想起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心中依然会涌起一股暖流。
如今,过年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是对亲情的眷恋;也是一个假期,一个回娘家的假期。
过年,就是回家,家里有爸妈。
□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