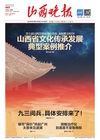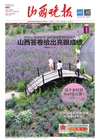最后的驻村工作队
1975年,我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在大队担任了通讯员。这年夏天,一场“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在全县展开。公社通知,县里要派一个工作队来我们村开展工作,搞这场运动。
头天晚上,大队召开了大小队全体干部会议,安排了工作队进村的各项事宜。党支部书记要求我,找好工作队住宿的家户,安排好队员的吃饭问题,并具体负责第二天工作队进村的接待任务。
来我们大队搞运动的工作队一共6人,都是从县各个单位抽调出来的,有农业、科技、公安、法院、银行等单位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其中,队长1人,指导员1人,队员4人。
在工作队进村的这天早上,我给他们找好了宿舍,是一家农户的三间大北房,工作队6个人全部住在这里,便于工作。他们的吃饭问题也安排好了,6个人,6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安排1个,全部吃派饭,挨家挨户管。那时候,工作队下乡,绝不搞特殊,全在老百姓家吃饭。他们也绝不白吃饭,上边有统一规定,吃老百姓的饭必须付饭钱,每顿饭一毛钱,四两粮票;一天是三毛钱,一斤二两粮票。他们下乡,村里只安排住处,对任何人都不提供铺盖。
吃过早饭,我和大队的干部们守候在大队部的院子里迎接工作队进村。大队部是原来的关帝庙,院子里有几株梧桐树,我们都站在梧桐树下等候工作队的到来。从9点半开始,队长、指导员先后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报到了。紧接着其他3名队员也陆续在11点前准时到来。这个时候,我们便开始忙碌起来,来一个安排一个,等把他们安排好,饭派好,就将近12点了。这时候,我们才发觉还有一个队员没有报到,大队干部和一个生产队长都在大队部焦急地等候。
天气炎热,人们在大队院子里的梧桐树下边乘凉,边谈论,等候着最后一名队员的到来。就在这个时候,从大队队部的院门外走进一个陌生人。远远望去,这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上去二十来岁,个子不高,穿着朴素,脚穿一双土布鞋,背上背着一个用细麻绳打成背包的铺盖,身上挎着一个军绿色的挎包,汗流浃背,精神抖数地来到我们跟前。原来他就是我们要等的最后一名工作队员。他叫刘延年,是县种子公司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他是唯一一名背着铺盖下乡的工作队员。他家离我们村15里,大学毕业不久,家里经济不宽裕,买不起自行车,无论去县里单位上班,还是下乡,他都是背着铺盖卷儿步行去的。我们赶紧接过他的铺盖,安排到住处,让生产队长领着他先去吃饭。
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工作队和村里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白天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晚上研究工作和开会,从来没有向大队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没有短缺过老百姓的饭钱和粮票,更没有吃过一顿公家饭。他们有事请假,当晚回去,第二天一早准时回来。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刘延年,他请假回家、回单位,还是那样步行着去,步行着来,从没有向同事借过自行车,更没有向大队开口解决交通问题。他的工作作风,深深地让村民们感动。
这件事情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了,我常常想起这段经历,眼前常常出现刘延年同志背着铺盖卷儿报到的影子,而且每每想起都回味无穷。那个年月,我们的干部是多么的廉洁、节俭啊,虽然生活艰苦,但是他们的精神面貌是那样的旺盛,工作作风是那样的过硬。
薛振堂(河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