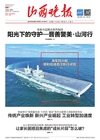家山有野菊
叶黄水瘦,寒意渐深,正是老家野菊盛开的时候。如往年那样,趁晴好的天气,我领着家人回乡踏秋。说是踏秋,其实就是到儿时熟悉的山洼里去,看野花、采野菊。
秋尾冬初,草木多半凋零,野棉花、野牵牛、鱼鳅串等零杂野花,却依然星星点点地开着,在日渐清癯的山野间,仍显得惹眼。而最抢眼的,还要数漫山遍野黄灿灿的野菊花。秋末冬初,田坎边,溪流旁,土墩上,山林间,凡能生长野草的地带,都密密匝匝地集聚着一丛丛野菊。随便走过一条小路,两旁都有摇曳生姿的野菊花;随便在一处田边地角蹲下来,身边都有野菊生香。一角土坡,一座沙墩,一堆乱石缝里,都有野菊在霜风里摇曳的影子。
午后的阳光,淡淡薄薄地洒下来,给金黄野菊镀上一层耀眼的亮光。农历十月间,小阳春的热气,让新绽的野菊蒸发出浓烈的苦香。这些带着野性的香气,引着我们徜徉在野菊缤纷的世界。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但我仍然记得哪片山坡野菊最密、哪道沟谷野菊最盛。记忆里的山野角落,模样也没怎么改变,簇簇野菊,还像当年那样热热闹闹地开,风里飘着的,还是当年那样的气息……
老家的村里人,都爱上山采野菊做菊花枕。每年母亲去山里采野菊,我总会提着小竹篓跟在她身后。做成一个菊花枕,需要两斤左右干菊花。我跟着母亲,哼着“野菊花,坡坡黄,又有外婆又有娘……”的民谣,采了一坡又一坡,采了一沟又一沟,从野菊初开,采摘到冬至前后。那些日子里,手上和衣襟上都沾满了野菊的味道。采回来的野菊,要摊在竹簟上晒干,才能填充在旧布枕芯里,做成苦香苦香的菊花枕。那时我家有四个菊花枕:爷爷经常失眠,奶奶患头风,睡不安稳。母亲给他们做的枕头就全用菊花。我和父母的枕头,则是在稻壳里混合些野菊花。记得那些年,床上有个菊花枕,连梦里都有香味。枕芯年年换,野菊也就年年采。
母亲采菊花时,还会顺带采点儿没开的野菊苞,做成野胎菊,留作泡茶和药引。母亲说,野菊味苦,要蒸过才行。母亲做菊花茶时,我常常守在灶台边看:先往铁锅里掺少许清水,再架上竹编甑箅,待旺火把水烧开,冒出腾腾热气时,就把野菊花苞均匀铺在甑箅上,赶紧捂严锅盖。蒸几分钟,就拈出,摊在簸箕里,搁在屋檐下通风的地方,自然风干后,存放在老竹筒里密封,就可用一整年了。
夏天,熬薄荷茶时,丢两朵野胎菊,特别解暑清火。要是有个头疼脑热、咽喉肿痛或眼睛眦糊之类的小毛病,喝上三两杯野菊水,症状自然消失。父亲似乎对野菊也很偏爱,一到夏天就泡野菊茶喝,杯里浮着的胎菊还很鲜活。我曾偷尝过一口,那苦味,很难下咽。
进城后,见过千姿百态的观赏菊。但我至今还是偏爱带乡土味的野菊。在我的眼里,野菊迎着山风长,顶着寒霜开,毫不娇气。尤其单瓣的花型,简约透着倔强的山野风骨。可以说,野菊的美,就美在那份天然的野气和野性。
眷恋家山,偏爱野菊。几十年来,我从未丢下过野菊情结。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野菊,便会生出亲切感,更会忍不住多看几眼。每年秋末冬初,我可以不看城里千姿百态的菊展,但一定会回到老家,去山坡沟谷里看野菊,顺便采些野菊做菊花枕;当然也会像曾经的母亲那样,蒸一瓶野胎菊留当茶饮……
也曾带回过野菊作盆栽,可总不见花开——或许,这就是野菊只爱丘山的本性吧。
□徐天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