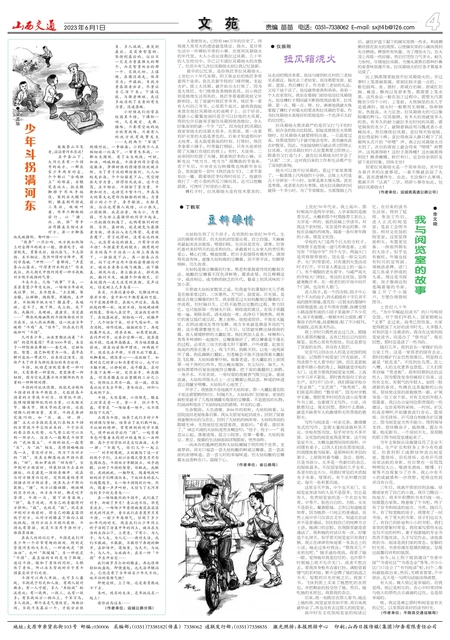拉风箱烧火
仪振刚
人类使用火,已经有180万年的历史了,西侯渡人类用火的遗迹就是铁证。烧火,是日常生活中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在使用风箱烧火的年代里,大人小孩应该都拉过风箱。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早已记不清拉风箱烧火的次数了,但其中有几次拉风箱烧火却让我记忆犹新。
最早的记忆里,是给铁匠李拉风箱烧火。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阳王铁业社的铁匠李带着两个徒弟,驻扎在新牛院的门楼西侧,支起火炉,搭上大风箱,就开始点火打铁了。因为是大铁匠,专门修理各类钢铁农具,而小铁匠则是修理生活用具的。铁匠李看着跟我祖父年龄相仿,见了面就叫铁匠李爷爷,铁匠李一看有人叫自己爷爷,心里那个高兴,就将我抱起来放在他拉风箱烧火的高椅子上。出于好奇,我就小心翼翼地询问是否可以拉他的大风箱,得到允许后就双手握住风箱拐使劲推拉,令人印象深刻的就一个字“沉”,因为他们的风箱比我家里烧火的风箱大很多。在那里,第一次看到炉火里的火焰是青色的,后来才知道那叫炉火纯青,是火温度最高的时刻。打铁时,铁匠李拿着小锤子,时常敲打钢砧,只有大徒弟抡圆了大锤打在烧红的铁上;有时,大徒弟、二徒弟同时抡圆了大锤,跟着铁匠李的小锤,不断发出“咣当当、咣当当”圆舞曲的节奏来。若干年后,中央音乐台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里面就有一首叫《铁匠波尔卡》,二者节奏如出一辙。跟着铁匠李玩得时间长了,他就给我打了一把小型的西瓜刀做玩具,还可以削糖甜甜,可馋坏了村里的小朋友。
煿杠子时,拉风箱烧火是有技术要求的。从走动的频次来看,祖母与嫁到杜庄村的三老姑关系最近。每次去三老姑家,祖母都要发面、起面、虚面,然后煿杠子,作为看三老姑的礼品。父母下地干活了,祖母就带着我和弟弟,弟弟一个人在家里玩,我坐在柴锅门前给祖母拉风箱烧火,祖母煿杠子期间就不断指使我添柴禾、拉风箱、紧一点、慢一点、停、拉,渐渐地我就大体掌握了煿杠子对柴火的要求和拉风箱的节奏,作为拉风箱烧火表现好的奖励是给一个色泽不太好的坨坨吃。
拉风箱烧火要求最严的是伯父打勺子的时候。铝合金的熔点比较低,铝锭直接放在火里煅烧时,拉风箱烧火就要特别注意,一旦温度过高,快要成型的勺子就可能会变形,甚至融化流在炉膛里,因此,当铝锭烧软后就必须立即停止拉风箱,无论风箱拉到什么位置都要立即停止。跟着伯父打造勺子,就在拉风箱烧火时学会了“认真”二字,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烧火可以放开拉风箱的,莫过于家里蒸馍了。一般蒸馍上汽再烧四十分钟,总体上大约是五十分钟至一个小时。如果是蒸大馒头馍,甚至是枣馍,或者更大的大枣馍,烧火拉风箱的时间就得一个多小时。为了节省煤炭,当蒸馍锅上汽后,就往炉盘下漏下的碳灰里倒一些水,和成稠粥状搭在炭火的周围,以使碳灰里的小碳块得到充分燃烧,释放所有热量。为了增加火力,在火顶上再搭一些好碳,然后任凭你力气多大,耐久力如何,尽情地拉风箱。当馒头蒸熟后那种扑鼻的麦香味弥漫开来,拉风箱烧火的任务才算基本完成了。
比上锅蒸馍更能放开拉风箱烧火的,非过事时上笼蒸碗莫属。席面比较丰盛一点的,一般包括鸡、鱼、猪肘、甜咸白扣碗、甜咸红扣碗、麻连、酥肉以及甜米等,都需要上笼水蒸。这些食品一般在加工过程中,需要大汽蒸腾至少四个小时。上笼前,大铁锅里的水几乎是盛满的,烧火时一般都用无烟煤,俗称钢炭,热值高,火力足劲,拉风箱烧火的可以像脱缰的野马,任其驰骋,有多大的劲就使多大的劲,有多久的耐力就拉多长时间的风箱。感觉锅里的水少了,就顺着锅沿用马瓢或者小水桶加水,然后继续拉风箱,直拉得天昏地暗,直拉得星转斗移,直拉得夜深人静只剩下了风箱两头舌片的“呼嘌”声。真正拉风箱烧火功夫到了,次日的席面上就会传来“啧啧”称赞声,这鸡蒸得软!这肘子蒸得糯!这扣碗蒸得到位!醇香嫩糯,软烂利口,定会给亲朋好友留下美好印象,回味无穷!
别看拉风箱烧火是一个简单劳动,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注意事项,一着不慎就会误了大事,甚至遗憾终生。由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认真”二字,琐碎小事亦如此,包括拉风箱烧火!
(作者单位:运城南高速公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