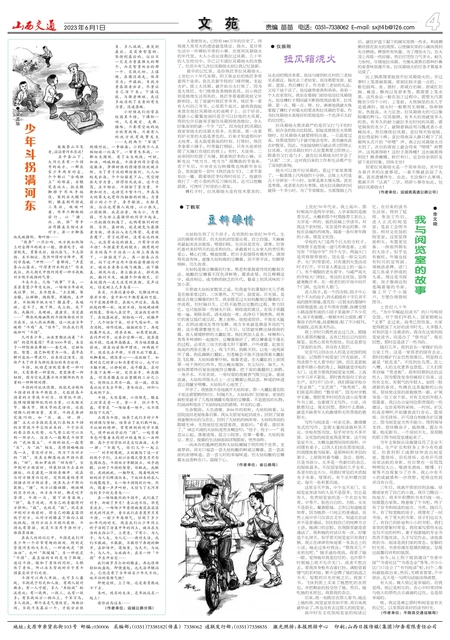豆瓣酿情
丁鹤军
大姑妈生育了五个孩子,在贫困的20世纪70年代,生活的确艰辛困苦。但大姑妈却坚强乐观、自立自强,天麻麻亮就起床洗衣做饭,喂猪扫院。生活虽是贫穷、清寒,但寄托着对美好明天的追求和向往,承载着对儿女家人的责任和爱心,精心打理,精盘细算,把日子拾掇得有模有样,调剂得有滋有味,就像大姑妈做的豆瓣酱,虽平常平淡,但醇厚绵鲜,历久弥香。
大姑妈是做豆瓣酱的行家,熟悉和掌握着传统的酿制方法。她酿的豆瓣酱不仅色泽鲜艳,酱香浓厚,而且稀稠适中,咸淡相应,成为物质缺乏的年代,餐桌上别具风味的下饭小菜。
尽管离大姑妈家数里之遥,但我童年的暑假时光几乎都是在她家度过的。三伏暑热,天气好,温度高,日光强,是最适合做豆瓣酱的时节。我亲眼见过大姑妈酿制豆瓣酱的工序流程,但时隔日久,已经不能想出完整的过程,努力回忆,也只能拾取一些镜头片段。刚收成的黄豆,在筛子里翻拣一遍,剔除杂质,清水浸泡一夜,洗净后下锅煮熟,将煮烂的黄豆捣烂成豆泥,裹上面粉,搓捏成团状,平放在大匾里,在阴凉通风处等待发酵。南方本来就是潮湿多雨的气候,适合霉菌繁殖生长。几天后,豆团就发酵出绿茵茵的霉,放入矮矮胖胖的大鎞缸里,按比例加入盐水、味精和八角等多种调料一起搅拌。豆瓣酱做好了,晒豆瓣酱是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在三伏天的毒太阳下暴晒、户外夜露。缸放在高高的两张长凳子上,鸡飞不到,狗跳不到,以免一泡鸡屎坏了酱,狗乱蹿跳打翻缸,但苍蝇会不依不饶地围着大鎞缸乱飞乱舞。大姑妈做事仔细,做酱老道,在大鎞缸的上面围罩一块干净的白纱布,防止蝇虫腐蚀、灰尘玷污。每天,大姑妈都要终而复始地搅拌豆瓣酱,把下面的酱翻到上面晒,一身汗水,不厌其烦。一旁玩耍的我被香气吸引过来,垂涎欲滴,大姑妈用筷头点上一点豆瓣酱让我品尝。鲜咸的味道直让我龇牙咧嘴,大姑妈开心地笑了。
开学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大姑妈家,那一大鎞缸酱在院子里还需要晒些时日。时隔不久,大姑妈串门回娘家,家里的碗柜里就多了几瓶玻璃罐头瓶装的豆瓣酱。不是值钱的礼物,但浸润和饱含了大姑妈纯洁的感情,朴实的心意。
生命脆弱,人生清瘦。2016年的初秋,大姑妈病重,从医院送回老屋准备后事。我从太原匆匆赶回故乡,回到了留着我童稚快乐的马思庄,回到了大姑妈的病床旁。大姑妈浑浊的眼睛无神、无助地怔怔地望着我。表姐问:“看看,谁回来了。”神志不清的大姑妈竟然含糊念叨:“侄子、侄子……”我悲从心起,落寞成殇。孤立小院里,往事一幕幕,大姑妈筛豆、煮豆、搅酱的生活画面却浮现眼前,恍然如昨。
一块冰冷的墓碑把我和大姑妈横隔于阴阳两个世界,支离梦碎,再无口福尝一尝大姑妈酿的鲜咸豆瓣酱,尝一尝浓浓的亲情味道,尝一尝儿时的幸福味道。但大姑妈酿的豆瓣酱永远香鲜在口,温暖于心。
(作者单位:省公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