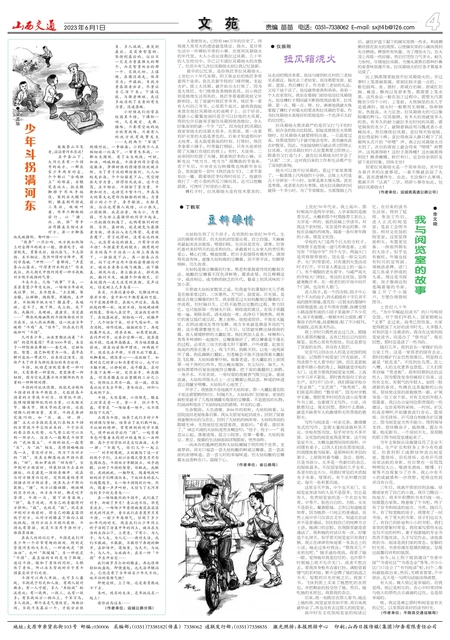我与阅览室的故事
李文晓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上高中。那时候高中是两年学制,入学采取的是推荐方式,大概和那个时期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是一样的。能到县城上学读书,对我这个农村娃,实在是件幸运的事。学校在县城的西南角,隔着一条叫青年路的小巷,便是文化馆。
学校的大门是两个巨大的方柱子,用铁管子造型成一道弓形牵连着,上面写有“平陆中学”四个大字。两扇大门是用铁管焊接的,顶头是一排尖尖的矛。大门时常紧闭,只有遇到大型活动时才打开,平日里人都走边上的一扇小门,有个瘸腿的老头看守。与威严高大的学校大门相比,旁边的文化馆,显得就寒酸许多。在一排老旧的平房中间开个门洞,也没有人看门。
进入院子,是一个四合院。院子中心有个不大的池子,砖头砌成有十字孔并不高的圆形围墙,莲花在一汪碧水的墨绿叶间娇艳盛放。池子外围有苗圃,纵横交错小路连接形成的小园子里栽种了不少花木。房子有廊檐,一根根木柱立成排,檐下靠房子的外墙,挂着橱窗,贴了不少报刊,有画报,还有美术作品。
我上学时只偶然进去过几次,跟随别人看那些橱窗,还有已经忘记内容的展览。虽然心里有些胆怯,但还是看完了里面的东西,并没有人阻拦。
完全可以自由出入的是文化馆的阅览室。记得那个阅览室门开在临街,不用进那个无人看守的门洞,而且是紧挨着青年路小巷的角上,隔路就是学校的大门,这更方便我到阅览室光顾。上高中学习并不紧张,那时教育面向工农业生产,实行开门办学。我们那届学校分“农业班”、“文艺班”、“体育班”,我们班是所谓的“数学班”。因为对学数学无趣,便把更多时间花在读小说等课外书上面。也豪情万丈写作,小说、诗歌都写过。现在回想,那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青年人的激情和无所畏惧的憨胆大。
写作与阅读是一对亲兄弟。激情爆发式的写作,急需大量阅读填补其不足。学校有图书馆,似乎对学生不多开放。文化馆的阅览室我是常客。这个阅览室不大,大概也就两间房的面积。中间摆有桌子,以供人们坐在那里阅读。四周摆放着书报架,是那种斜形多层的架子,上面陈列着书籍、杂志、报纸。只是书很少,大多是一些新旧的杂志。而报纸最多,不仅国家级的几乎全有,各省市的也不少。用那时常见的木质报夹子夹着,厚厚的,有个长杆螺丝固定,每天一张积累而成。
这里全天开放,中午也不关门。在阅览室里读书的人虽不是很多,但总是有人。负责阅览室的是一个北京女知青,中等个,肤色白白的,方脸,头发不是很长,戴着眼镜。之所以知道她是知青,因为她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虽然上高中学习汉语言文学,知道北京话并不是普通话,但比较自己的纯粹方言土语,她满口的京腔,在我眼里就是普通话了。我和她的对话只有一次,好像是个礼拜天。似乎那天阅览室只有我们俩。我正在津津有味地看一本杂志上的小说,她走过来对我说:“帮我买几个水煎包吧。”随手递给我钱,我看了她一眼,觉得她对我是信任的。也许那个时候她上班不允许关门,或者不想出去,看我浑身粗布衣着打扮,满脸冒着傻气的农村娃,断不会携了她的钱逃之夭夭。短暂的目光对视之后,我放下书,飞快到街上买来了她想吃的水煎包,并把剩余的钱交给了她。然后,她吃她的水煎包,我看我的杂志。
后来,我一如既往在那儿看书,她还上她的班。阅览室里亦如平常。再后来我就毕业了,再也没有去过那儿的阅览室。
高中时在文化馆阅览室的阅读记忆,在后来的读书生活里,得到了延续。参加工作后,进入正式的阅览室,是县工会图书馆。相对文化馆的阅览室,这里显得面积大,布置更完备。一排座西朝东的大房子,似乎也有廊柱,外墙也挂有时兴的宣传画、领袖语录牌。进门是几张桌子拼成的大桌,周边是书报架。房子靠南边则是隔着墙的书库,墙上开了个小窗户,方便办理借阅图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口号响彻全国,对于我们年轻人,国家刚刚从“文革”走过来,高考已经恢复,大家觉得耽误了大好的读书时光,大多数人对知识是十分渴求的。我没在这里的阅览室读书,而是办了“借书证”。现在回想,那时还是读了一些书的。
随后几年,我到县东一家煤矿的办公室工作。这是一家很老的国有企业,那时的煤矿行业仍然很落后,明显特点就是“脏乱差”。不仅到处乌黑,乱七八糟,人的文化素养也很低,工人们常常自喻“黑老粗”。我和同期到达的这些人,因为要改变身份被招工而来。这些有文化、有朝气的年轻人,如同一股清新的春风,吹拂在这条偏僻的山沟里,很快使这里的面貌焕然一新。矿领导是一位工农干部,对有文化的年轻人很器重。我以办公室岗位职责提的一些建议,也容易得到采纳。一时间,矿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流行音乐,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相继在矿区建立。图书阅览室当然不能少。得到领导支持,很快腾房子,搞修缮,置办书架,购买新书,一个房间不大,很简陋的职工图书阅览室建起来了。
当年文体娱乐设施建设花了企业不少钱,生产矿长和财务上多少有些意见。但看到职工成群结伴进出阅览室,篮球场、羽毛球场,还有乒乓球房里活跃的身影,往日聚在一处骂骂咧咧侃大山,喝酒发酒疯、赌博、打架等不良现象少了许多。我心中有不小的成就感和一丝欣慰,觉得这些钱并没有白花。
三年后,我离开那里回到县城。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小窝,我尽力腾出一块地方,将多年积攒的书本归拢一块,结婚置办家俱,特意做了个书柜,终于有了存书和阅读的地方。当然,随后几年,有了较宽敞的房子,我便有了一间书房,有了更大的书架。孩子们也长大了,有自己的卧室和小小的书柜。我们家里的景象时常是,我伏案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材料,妻子抱着她的专业书孜孜不倦攻读,儿子写完作业,读他喜欢的书。阅读是我们家的常态,安静的时光里,书香弥漫在低矮的陋室,呈现出温馨而祥和的氛围。
如今,从上到下提倡建设“书香中国”“书香社区”“书香企业”等等,不少小区门口设立了“书刊阅读”柜,扫个二维码就能取出来,然而,光顾者寥寥,个中原由,也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得清楚。
有人说,被人惦记是幸福的。而我觉得,惦记是相互的。在心中时常回味与他人的那些点点滴滴的过往,也是很幸福的。
唉,我还是难忘那时和阅览室有关的记忆,以及那段美好的读书时光。
(作者单位:平陆县交通运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