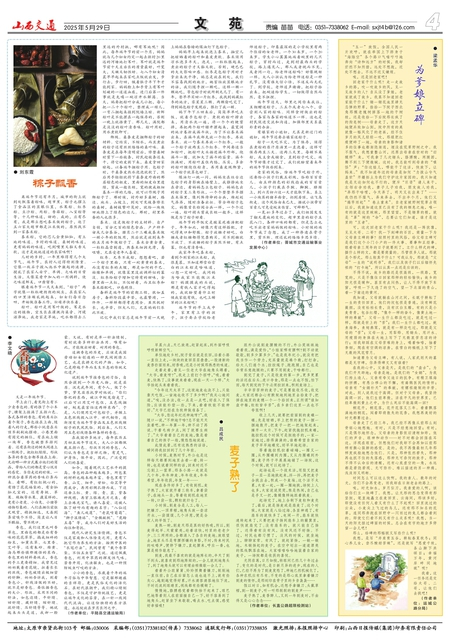麦子熟了
吕成民
早晨六点,天已放亮,赶紧起床,到外面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单位地处乡村,院子背后就是农田,沿着小路一直往上走,一块块的麦田层层叠叠,一股清新的麦香扑面而来,好香哦,还是小时候那熟悉的味道。
走着走着,看见一位老大爷在地角头蹲着,“大爷,看麦呀?”,我走上前打个招呼,“哦,看看麦,快熟了,没事就来看看,现在一天一个样。”大爷抬起头来看看我。
“今年这天太旱了,这坡地麦也浇不上,只能靠天吃饭,一亩地也收不了多少啊?”我关心地问道,“唉,没办法,收一点是一点吧,好在入了保险,应该能补偿一些,下来,看看秋能不能种好。”大爷已经在为秋种做准备了。
“大爷,您这年纪还种地呀?”,我随口一说,“不种地干啥?总不能天天坐着吧,种一年算一年,种不动了再说。干着毛病少点,闲了就要生病了。”大爷看着自己的麦地,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般,慢悠悠地说道。
此情此景,还有这熟悉的话语,瞬间将我拉回到了几十年前。
小时候,麦熟时节,外公也是这样每天都要到地里去看一看、转一转,也是说着同样的话,回来时还不忘割上一筐草。那条小路一走就是几十年,年年种麦、年年收麦,年年希望、年年收获,年复一年……
现在条件好多了,有收割机,麦子熟了,大家就开着三轮车,拿着袋子,在地头一坐,等着收割机在地里一转,口袋一张,颗粒就归仓了。
小时候,割麦全是人工,每人一把镰刀、一顶草帽,地角头放一壶凉开水、一袋馍馍、几个洋葱,便是全家人的早饭了。
麦熟一晌,割麦天那是真的好热哦,所以,割麦得起早。天蒙蒙亮,趁着凉快,村里的老老少少、三三两两的,全都涌入了各自的麦地。放眼望去,地里头尽是弯腰挥镰的身影,不时,传来村民的吆喝声,便停下镰刀,直起腰来,呼应一番,也算是稍作歇息了。
割麦,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地阵长的,半天了割不到头,就喜欢割那地阵短的,一会儿就到地角头了,到了地角头就可以有理由稍微歇一会儿了。
看着外公跟舅舅、妗妗挥舞着镰刀,刷刷地一直往前,自己在后面怎么追也追不上,就有些灰心,越割越觉得好累,汗水滴答滴答地往下流,不时还流到眼睛里,视线都有些模糊了。
慢慢地,胳膊感觉着都快抬不起来了,眼巴巴地等着别人在前面接自己一下,好不容易到了地角头,赶紧坐下来歇歇,喝点水、吃点馍,感觉好幸福哦!
跟外公说割麦腰酸的不行,外公笑眯眯地看着我,满是爱怜,“小娃家哪有腰啊?割不动就歇歇,割多少算多少。”也是我年纪小,就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劳力,充其量就是凑个数,打打杂,给大人们递个水、拉拉绳子、跑跑腿,自己也是非常乐意跑腿的,只要不用割麦,干啥都行。
割完了麦子,只是收麦的第一步,更多更累的活还在后头。虎口夺食,那是一点也不假,怕下雨,每天割完的下午必须拉回来,积到麦场上。
辛辛苦苦种的麦子,可是要能收尽收,收完麦,大家还都会心有默契地到地里去拾麦子,把掉在地里的麦穗一个一个拾回来,正所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乡亲们这里一点也不
夸张啊!
收上几天,就要把前面割的麦碾一碾。先是晾晒,早上把积的麦子一捆一捆地散开,把麦子一把一把地架起来,摊开一大片。下午,赶紧找拖拉机来碾,拖拉机这个时候可是挺抢手的,一家一家地过,排得满满的,谁都希望自家的麦子早早地碾完,好早早地起场。
等着拖拉机拉着碌碡,一圈又一圈,从外圈碾到内圈,又从内圈碾到外圈,麦子终于平展展地铺了一场院,这个时候,就可以起场了。
起场也是一个技术活,用股叉把麦子一层一层地挑起来,抖一抖,再把麦子全挑出去,积成一个麦垛。这个活不太累,大家一起,一圈一圈地挑,场院上人也多,大家说说笑笑,煞是热闹,自己也是手叉一把,像模像样地跟着挑麦。
起场完了,地上全剩下麦粒和麦壳了,最后,就是扬麦或是扇麦了。这个时候,大家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扇车的就快多了,电闸一开,扇车就快速转起来了,只要把麦子扬到扇车上的簸箕里,很快就扇完了。没有扇车的,就只能自己扬了,还得看有没有风,没有风还不好扬。不过,村民也都习惯了,没风的时候,就坐地上,聊聊家常。有风了,就赶紧扬,一锨一锨地,木锨扬起的麦子,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漂亮的弧线飘落在地,大家嘻嘻哈哈地装着自家的麦子,一场院都是收获的喜悦。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已然几十年过去了。变化的是时代,是日新月异的进步,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为了割麦发愁了,种地已然机械化了,各种农机应有尽有。不变的是那心底里拿着镰刀割麦的情怀,是那刻印在骨子里的乡音袅袅……
假以时日,如有机会,还想手拿镰刀、头戴草帽,割一割麦子,听一听那刷刷的割麦声……
麦子熟了,麦香醉人,又到一年割麦时,不由得又是心心念念……
(作者单位:长直公路超限检测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