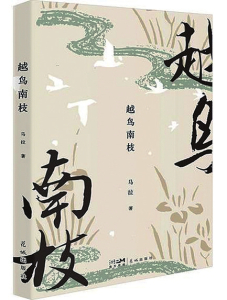爱与回归的现世书写
马拉近年的散文和小说我都熟读过,最深的感受就是,他就像天生的“心灵捕手”,眼光锐利,甚至是毒辣,总能精准窥探到每个人的隐秘心事、难言的困境,再机巧灵动地诉诸笔端,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的模样。
他最新的中篇小说集《越鸟南枝》包括《托体》和《如归》两部中篇,以生意人、文学教授、女大学生、小镇青年等为对象,展示了当今社会的种种面貌。两篇风格迥异,母题都是关于爱与回归。这也是书名取自“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深层意蕴:既为自然习性的写实摹画,亦有古典溯源的情感内核。其结构精巧,要素间彼此映衬,彰显出马拉对小说艺术的审美创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贴合了当下的精神图景。
《托体》写了易过庭在妻子弥留之际拼力寻找失散多年的儿子的故事,以“寻找”与“告别”的双线叙事,串联起两代人被命运错位分割的亲情,探讨了血缘羁绊的宿命感与人生无常中的遗憾与和解。父亲用半生执念寻找遗失的亲情,儿子在未知中完成了对生母的终极告别,两条线索交织出亲情在时间与距离中的坚韧与脆弱。小说核心的悲剧性在于“相见不相识”的错过,但深层传递的是对人生遗憾的接纳,生命中的缺失与错位,最终会成为个体成长的底色,让人体悟到亲情的多元形态与生命的厚重。《托体》的叙事非常有特点,里面有“荒蛮故事”“铁城歌谣”两个子故事,同时,两个故事的线索并非独立进行,而是显性交织。
“荒蛮故事”聚焦父亲的“寻找”,易过庭的焦灼奔波,是半生执念的集中爆发,这条线索带着强烈的时间紧迫感和无力感,结果是求而不得。“铁城歌谣”围绕着儿子的殡葬故事展开,这条线索看似与“寻找”线毫无交集,实则在时空维度上形成了呼应。孟一舟的岳父就是易过庭托付的寻亲人,且孟一舟也亲自入殓了生母,他们本来可以相认,但“得而不知”。小说还注入了生母与养母爱意交织的隐形双线:孟一舟以职业的虔诚,给予了赵曼生最郑重的体面,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生母生前的重逢遗愿。叙事中留有大量留白,父子最终是否相认?孟一舟到底是不是易过庭和赵曼生所生?又或梅毅柳其实就是孟一舟的生母?均未明确交代。这种留白让故事的遗憾感突破了文本边界,也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契合了“接纳遗憾”的深层主题。
《如归》以中年教授朱亦敬与女学生顾乙沫的情感纠葛为主线,深度刻画了人性的复杂与脆弱。朱亦敬有对激情的执念,顾乙沫有短暂的良知觉醒,最终都在命运的连锁反应中沦为悲剧的制造者与受害者。朱亦敬内心始终“意难平”,他是合格的教授、尽责的丈夫,却唯独不是“被热烈爱过”的自己。
生活乏味的朱亦敬将顾乙沫的“漂亮奔放”等同于打破寡淡生活的救赎,实则是对现实的逃避与对人性的误读;而顾乙沫本质是原生父爱缺失,叠加幼稚的生活认知,最终在欲望、背叛与暴力的交织中,酿成家庭破碎的悲剧。小镇青年周惊雷和唐海洋则是同一类人。顾乙沫、周惊雷、唐海洋三个年轻人的人物弧光里藏着典型的成长阵痛和人性挣扎。《如归》揭示了幻想与现实的撕裂,暗示了“寡淡”不是生活的枷锁,而是藏着责任、克制与温情的生命底色,强行打破,可能会坠入无序与毁灭的深渊。
掩卷静思,原来所谓犀利的眼光,是看透世情后,落笔描摹的真诚。正是这般锐利如刃的眼睛,才能让文字跳出了单薄的叙事,让那些众生百态有了筋骨。《越鸟南枝》既有对人性的深度醒察,也有对生存本质的哲学思辨,它让读者在角色的体悟中照见自身,也在悲喜剧的余韵中,重新审视“平庸”日常的珍贵与厚重。
吴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