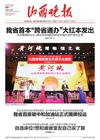三十年前沁水乡村长燃不息的灶火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一家三口陪老岳父回他老家山西沁水嘉峰镇永安村探亲。从晋城下了火车,便坐上接我们的吉普车顺利到家。岳父五弟家住房比较宽敞,我们就入住他家。
厨房坐落在正房西侧,炉子是自己用砖盘的。五叔在家里是甩手掌柜,五婶是家里的大厨。她干活利索,做饭麻利,灶台也抹得干干净净。案板不用时,总有一个连体的盖子扣着,卫生美观。住下之后,我有一个吃惊的发现:村里有煤矿,就是豪放,灶火长燃,壶水长开,他们没有“封火”的概念。炭烧乏了,再添上一灶新炭。从早到晚,只要不做饭,一个大铁水壶就坐在炉口上,沸腾的水变成了蒸气,随风飘散。这场景,让从小经历过拣柴火、搂树叶的我,很是心疼。心疼那黑黝黝的炭块,白白地浪费了光和热。
我问五婶,咱们怎么从早到晚都不封火呢?五婶说:这样用火方便。咱们村就有煤矿,用煤便宜方便,基本上家家都不封火。夜以继日,灶火长燃。
我们所在的宿舍区在没有通煤气前,家家都要打煤糕、和煤泥,做完饭就封火,用火时再捅开。像岳父老家这样的豪放用煤,让我大开眼界、自叹弗如。我暗自揣测:可能是让这长燃的灶火,昭示他们红火富足的生活?
近30年过去了,我的脑海里始终忘不掉岳父老家那长燃的灶火。如今当年那种“灶火长燃”的场景怕是再难见到了。节能减排应该已经是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了。
解延忠(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