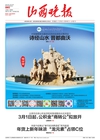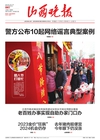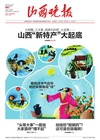山西大学首次书展
1962年国庆节前夕,山西大学中文系和化学系几位爱好书画的同学聚在一起聊天。当时山西省第一届书法展已经在山西省博物馆开幕,我和六一级乙班同学钮宇大的作品有幸参加展出。当时我刚22岁,是参展人员中年龄最小者。我向大家提出咱们能不能也在学校搞一个书画展?大家一致赞同,建议以校团委的名义主办。第二天请示校团委同意后,我们就着手准备起来。
1962年,困难时期尚未过去。一切供应都十分紧张。宣纸,只有桥头街美术服务社的柜台上可以见到,但价格较贵,学生根本买不起。墨汁,街上文化用品商店里倒是不少,但都是清一色的太原制造的“双塔牌”,质量较差,时间长了还散发臭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用有光纸和薄一点的道临纸。大部分同学写在有光纸上,一部分同学用道临纸,用勾涂的方法造出黑底白字的效果,黑色涂得非常均匀,如同碑的拓片,看起来别有风味,很是夺人眼球。在展出的少数绘画作品中,也有少数人用宣纸,显得格外高雅。
为了提高展览的品位,我亲自上门请来了几位先生的作品。一位是赵延绪,字缵之,他是有七代学生的美术教师,更是一位资深的画家,传统功力很深,尤其是墨色运用过人。他常背抚古人之法,对任伯年、石涛等情有独钟,所出手的作品往往可以乱真。他曾留学日本,素描很棒,我曾在姚奠中先生家中看到过他用碳素笔为章太炎先生画的画像。我上门说明来意,他很痛快地从书架上拿出一幅已裱好的画交给我。我表示展完之后原物奉还,他笑着点了点头。杨秀珍是山东青州人,她早年就在北京上艺术专科学校深造,且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白石先生曾为她刻有名章“秀珍”一枚,姚奠中为她刻“白石老人弟子”一印。每每作画她总是两枚印章并用:“白石老人弟子”下钤以“秀珍”。一朱一白两方印章配在画作签名下方,一目了然,人们在欣赏画作之间便了解了她的身世。我和杨吉魁去她家求她参展,她画了一张万年青,以祝新中国成立一十三周年。
宋光祥先生是历史系的教授,他以草书见长。他的草书流利飞动,有传统的厚重,又有自己的飘逸。我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他家。他正在备课,对邀请他参加书画展,感到有些意外。他问了展览时间和哪位老师参展后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说写好后会按时送到教工俱乐部。第二天下午,他就完成了,写的是草书四条屏,虽然写在道临纸上,纸光滑又吃墨差,但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姚奠中先生是我们的古典文学老师,他以魏碑为基,行书超众。他很支持我们举办书展,并将他收藏的齐白石先生画的一副“虾”拿出来展示。这幅画虽然不大,但很精致,姚奠中先生在“诗堂”上题了一首诗,对画进行了评赞,更加强了其艺术效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白石老人的真迹,如获至宝,布展时把它放到了第一位。
怎么能突出姚先生的作品呢?我们把有光纸十二张接到一起,如同教工俱乐部北墙上的电影银幕一样大,因道临纸太厚,不好黏接,只能选用较薄又有点水洇的有光纸。姚先生脱掉鞋子,站在接好的纸上,用大号斗笔写了一首毛主席和柳亚子的词《浣溪沙》。这首词内容写国庆节,上下阕共四十二字,四十二个字写在接起来的十二张纸上,每个字得多大啊!他站在纸上端详片刻,便弯腰疾书起来,每个字尺余,一气哈成,如行云流水,遒劲有力,大小有致,书到最后落笔时围观的师生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么大幅的诗书无法装裱(当时也找不到装裱的地方且也无钱裱),我们把它缀在银幕上,挂起来后,效果极佳,成为整个展览的提神之作。
赵望进(太原)